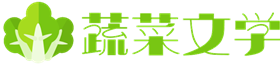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沈砚辞就醒了。客栈的窗户对着一条小巷,巷子里已有早起的商贩推着小车走过,吆喝声混着晨光,把江宁城的热闹慢慢铺开。他轻手轻脚起身,怕吵醒还在熟睡的柳青云三人,拿着洗漱用具走到客栈后院。
井水带着清晨的凉意,泼在脸上让他瞬间清醒。他摸出怀里的小布包,里面是苏婉娘给他缝的帕子,上面绣着小小的 “安” 字。指尖蹭过细密的针脚,他想起出发前婉娘反复叮嘱 “到了江宁记得照顾好自己”,心里泛起一阵暖意 —— 不知道她收到信没有,家里的桑树苗有没有栽活。
“沈兄,起得这么早?” 柳青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也拿着书,显然是准备找个安静地方复习,“我刚才问了客栈掌柜,贡院登记要到巳时才开始,咱们不如先去附近的书坊看看,听说那里有近年乡试的优秀策论集,或许能参考参考。”
“好主意!” 沈砚辞眼睛一亮,连忙擦干脸,“我去叫李默和张修,咱们吃完早饭就去。”
四人在客栈楼下简单吃了些包子粥,就往书坊赶。贡院附近的书坊格外热闹,挤满了各地来的考生,有的在翻找复习资料,有的围在一起讨论题目,空气中满是紧张又兴奋的气息。沈砚辞在书架上翻找,很快就看到了柳青云说的策论集,封面印着 “江宁乡试近五年佳作选”,他连忙拿下来,又顺手取了本《农桑辑要》—— 里面或许有之前在桑林没问到的细节。
“沈兄,你看这个!” 张修拿着一本小册子跑过来,脸上满是惊喜,“是贡院的布局图,还有考试注意事项,比如笔墨要自己带,不能夹带,甚至连考棚里的桌椅高矮都写了,咱们提前看看,到时候就不慌了。”
沈砚辞接过小册子,仔细翻看起来。里面不仅有布局图,还有往届考生写的 “应试经验”,比如 “考棚风大,要带件厚些的外套”“干粮别带太油的,容易渴”,都是些实用的提醒。他心里暗暗记下,想着回头要跟另外三人一起整理份 “应试清单”,免得漏了什么。
巳时一到,四人往贡院走去。江宁贡院比吴县文庙气派得多,朱红大门前立着两尊石狮子,门楣上挂着 “江南贡院” 的匾额,阳光下透着威严。登记的队伍排得很长,大多是穿着长衫的考生,还有些考生身边跟着书童,手里提着精致的食盒和笔墨箱,一看就是富家子弟。
“哟,这不是柳兄吗?怎么跟这些穷酸凑在一起?” 一个尖细的声音传来,说话的是个穿着锦缎长衫的少年,身边跟着两个书童,正用轻蔑的眼神看着沈砚辞四人。
柳青云脸色一沉,却没说话,只是往沈砚辞身边靠了靠。沈砚辞认得这种眼神 —— 和王元宝当初看他的眼神一模一样。他握紧手里的策论集,没理会少年的挑衅,只是低声对柳青云说:“别跟他一般见识,登记要紧。”
那少年见他们不搭理,冷哼一声,带着书童插队走到前面。队伍里的考生大多敢怒不敢言,只有一个老秀才低声骂了句 “仗着家里有钱,没点规矩”。沈砚辞心里叹了口气,却也明白,在这江宁城,这样的事恐怕不少,只能自己多加小心。
登记很顺利,官差核对了身份,在名册上勾了勾,又给每人发了块木牌,上面刻着考棚编号 —— 沈砚辞是 “寅字三号”,离贡院大门不算远,倒是方便。拿着木牌,四人往回走,柳青云才低声解释:“刚才那人是常州知府的儿子,叫赵文华,之前在常州就总爱欺负寒门考生,没想到在这里又遇上了。”
“别管他,” 李默拍了拍柳青云的肩膀,“咱们好好考试,只要考中了,将来总有机会让这些仗势欺人的人知道,学问不是靠钱堆出来的。”
回到客栈,四人把从书坊买的资料摊在桌上,开始分工整理。柳青云负责梳理 “吏治” 相关的策论要点,李默整理 “水利” 的实际案例,张修汇总应试注意事项,沈砚辞则重点完善 “农桑” 策论,把从桑林农妇那里听来的细节加进去,又补充了《农桑辑要》里的内容。
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客栈掌柜送来晚饭,四人才停下笔。简单吃了饭,沈砚辞拿出笔墨,想给苏婉娘再写封信,告诉她自己已经顺利登记,一切都好。可刚写了两句,又停下笔 —— 不知道地址能不能寄到,万一寄丢了,反倒让她担心。他犹豫了半天,还是把信叠好,放进怀里,想着等考完试,亲自带回去给她看。
夜里,客栈里的灯亮到很晚。沈砚辞坐在桌前,手里捧着那本乡试佳作选,仔细研读里面的策论结构。那些优秀的策论,不仅论点清晰,论据扎实,还能结合当下的时局,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比他之前写的要成熟得多。他一边看,一边在笔记本上记下好的句式和论点,准备融会贯通到自己的策论里。
“沈兄,你也还没睡?” 柳青云端着一杯热茶走过来,放在他手边,“别看得太晚,明天还要早起复习。我刚才看了你的‘农桑’策论,已经写得很好了,尤其是桑林管理那部分,比我之前看到的任何一篇都具体。”
“还是有不足,” 沈砚辞放下书,喝了口热茶,“比如如何平衡桑蚕养殖和粮食种植,我还没想清楚。要是把太多地用来种桑,粮食就会不够,可只种粮食,百姓的收入又会减少。”
柳青云想了想,说:“我倒觉得可以引用‘桑基鱼塘’的例子,就是把桑林种在鱼塘边,桑叶喂蚕,蚕沙喂鱼,塘泥肥桑,这样既能种桑养蚕,又能养鱼,还不耽误种粮食,一举多得。我在常州见过这样的模式,效果很好。”
沈砚辞眼前一亮,连忙拿起笔,把这个例子记下来:“这个例子太合适了!柳兄,真是多谢你,不然我还卡在那里。”
“都是同窗,不用客气。” 柳青云笑了笑,“咱们互相帮忙,才能都考出好成绩。”
夜深了,客栈里渐渐安静下来。沈砚辞把策论草稿收好,躺在床上,却没有立刻睡着。他想起苏婉娘,想起吴县的茅草屋,想起村口的老槐树,心里满是期待 —— 等考完试,他一定要带着婉娘来江宁看看,看看这江南贡院,看看这热闹的街市。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桌上的策论集和木牌上。沈砚辞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这次乡试能顺利考中,希望能早点回去,和婉娘一起,把日子过成他们期待的样子。
江宁城的夜,带着几分繁华,也带着几分紧张。再过几天,这里就将迎来一场重要的考试,无数像沈砚辞一样的寒门学子,将在这里书写自己的未来。而沈砚辞知道,他的未来里,不仅有自己的抱负,更有对苏婉娘的承诺。他必须全力以赴,不能辜负这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