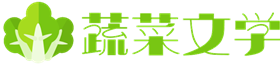城南的“回春堂”还亮着灯,药童正踮脚收拾药柜,见徐祯和扶着沈明月进来,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计:“徐小姐?这都快关馆了,是哪里不舒服?”
“她伤口裂了,麻烦李大夫看看。”徐祯和将沈明月扶到诊床坐下,自己则找了张竹凳挨着坐下,目光落在墙角那盆半枯的兰草上——上次来还是去年深秋,姑父咳嗽不止,她来抓过几服润肺汤,那时这盆兰草还郁郁葱葱的。
李大夫从内堂走出来,花白的胡子上沾着药渣,看到沈明月肩头的血迹,眉头皱了皱:“又是刀伤?你们这些年轻人,就不能让人省点心?” 嘴上抱怨着,手却利落地解开她的衣襟,露出缠着布条的伤口。
布条一解开,徐祯和倒吸一口凉气——原本缝合的伤口裂了道寸长的口子,血珠正往外渗,周围的皮肉泛着红肿。李大夫拿出烈酒消毒,沈明月疼得闷哼一声,额头上瞬间沁出冷汗。
“忍着点。”李大夫头也不抬,“这伤口再拖下去要发炎,得重新清创缝合。” 他转身从药柜里抓出几味草药,扔进石臼里捣烂,“这是止血的,先敷上。”
药糊敷在伤口上,带着一丝清凉,沈明月紧绷的肩膀微微放松。徐祯和递过一块帕子,让她擦汗,目光不经意扫过她腰间露出的半截玉佩——正是那枚拼合完整的莲花佩,此刻在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
“这玉佩……”徐祯和迟疑着开口,“你一直带在身上?”
沈明月低头摸了摸玉佩,嘴角牵起一抹淡笑:“母亲走得早,就留了这个给我。小时候总觉得它硌得慌,想摘下来,父亲却说‘这是念想,等你长大了就懂了’。现在才算真的懂了。” 她指尖划过玉佩上的刻痕,“你看这莲花,花瓣上的纹路多细,当年母亲说,这是她和父亲定情时,父亲亲手刻的。”
徐祯和想起英国公府那半块玉佩,忽然明白有些物件的意义,从不在它的价值,而在它承载的时光——就像姑父书房里那本被翻烂的《南疆舆图》,页脚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后来才知那是他年轻时跟着沈将军行军时记的;又像二姑母梳妆台里那支断了齿的桃木梳,她总说“这是当年沈夫人送的”,语气里带着连自己都没察觉的怀念。
李大夫缝合伤口的动作很轻,针穿过皮肉时几乎听不到声响。他忽然开口:“你们说的沈将军,是不是十年前守南疆的沈毅?”
沈明月猛地抬头:“您认识我父亲?”
“何止认识。”李大夫叹了口气,往伤口上撒了层白药,“我当年在军中当军医,沈将军中箭那次,还是我给他取的箭头。” 他指节敲了敲诊床,“那箭上淬了毒,将军却硬撑着指挥完战局才肯躺下,后背的肉都烂了,愣是没哼一声。”
徐祯和心头一动:“那您知道……沈将军被定罪前,有没有什么异常?”
“异常?”李大夫想了想,“倒是有件事挺奇怪。他出事前三天,让人给我送了个木盒子,说‘若我三日未归,就把这个交给英国公’。可第二天就传来他通敌的消息,我哪敢送?后来盒子被兖王府的人搜走了,听说里面就放了半块碎银。”
半块碎银?徐祯和与沈明月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疑惑——沈将军要送的,绝不可能只是碎银。
“那碎银上有没有刻字?”沈明月追问。
“刻了,好像是个‘南’字。”李大夫用沾着药粉的手指在桌上画了画,“当时觉得莫名其妙,现在想来,怕是藏着什么暗号。”
“南……”徐祯和默念着这个字,忽然想起姑父书信里提到的“南疆密道图”,“难道与南疆的密道有关?”
沈明月却摇了摇头:“父亲对南疆的地形了如指掌,根本不需要密道图。” 她忽然顿住,眼神亮了起来,“我知道了!是‘南记粮铺’!父亲在南疆时,总去那家粮铺买米,老板是个跛脚的老兵,说跟父亲是同乡。”
李大夫已经缝合好伤口,正在包扎:“南记粮铺……我好像有点印象,听说后来被一场大火烧了,老板也不知所踪。”
“烧了?”徐祯和皱眉,“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沈将军出事的第二天。”李大夫将最后一圈纱布系好,“当时只当是意外,现在看,怕是被人故意烧的。”
药童端来两碗药汤,黑褐色的液体冒着热气,药香弥漫了整个医馆。沈明月接过药碗,刚喝一口就被苦得皱眉,徐祯和连忙从怀里掏出颗蜜饯递过去——那是早上出门时画春塞给她的,说“万一遇到沈小姐,让她尝尝”。
“画春呢?”徐祯和忽然想起,从药庐分开后就没见过她。
沈明月含着蜜饯,含糊道:“我让她去查福伯的底细了。那个老东西既然是兖王安插的,府里肯定还有他的同党,不揪出来始终是隐患。” 她顿了顿,看向徐祯和,“你二姑母……真的和兖王勾结了?”
提到二姑母,徐祯和心里像被什么堵住了。她想起小时候,二姑母总偷偷给她塞糖,还教她叠纸鸢,说“祯和的纸鸢要飞得比谁都高”。可那些书信上的字迹不会假,姑父的供词里也提到“内子曾助兖王转移军械”。
“不知道。”徐祯和低声道,“或许……她有苦衷吧。”
李大夫收拾着药箱,闻言插了句嘴:“这世上哪有那么多苦衷?大多是选了容易走的路罢了。” 他看向窗外,夜色已深,“就像我这盆兰草,以前总想着多浇水能长得好,结果烂了根,后来索性不管了,反倒抽出新芽了。”
徐祯和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墙角,那盆半枯的兰草,根部果然冒出了一点嫩绿的芽尖,在昏黄的灯光下,透着股倔强的生机。
离开医馆时,街上的灯笼大多已熄灭,只有更夫的梆子声从远处传来,“咚——咚——”,敲得人心头发沉。沈明月走得有些慢,伤口的疼痛让她额角冒汗,徐祯和便扶着她,一步一步慢慢走。
“你说,父亲留的那半块碎银,会不会藏在南记粮铺的废墟里?”沈明月忽然问。
“有可能。”徐祯和踢开脚边的石子,“等你伤好了,我们去南疆看看。”
“去南疆?”沈明月停下脚步,眼中闪过一丝向往,“我还没去过呢。父亲说南疆的花全年都开,还有会唱歌的鸟。”
“那我们就去找会唱歌的鸟。”徐祯和笑了笑,“再看看你说的那个跛脚老兵还在不在。”
两人走到岔路口,沈明月住的客栈在东边,徐祯和要回侯府得往西走。灯笼的光晕在地上画出两个重叠的圆,又随着脚步慢慢分开。
“明天我去找你?”沈明月问。
“嗯,我让画春备些点心。”徐祯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才转身往侯府走。
侯府的门虚掩着,门房打着哈欠,见她回来,连忙迎上来:“小姐,您可回来了!二姑母……二姑母傍晚回来过,留了个木匣子在您房里。”
徐祯和心里一紧:“她人呢?”
“没多待,放下匣子就走了,说让您务必看看里面的东西。”门房搓着手,“看着像是哭过,眼睛红红的。”
徐祯和快步走进内院,推开自己房门,桌上果然放着个梨花木匣子,锁是开着的。她深吸一口气,打开匣子——里面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几件旧物:一件洗得发白的孩童肚兜,上面绣着只歪歪扭扭的兔子;一本泛黄的《女诫》,扉页上写着“祯和亲启”;还有……半块刻着“北”字的碎银。
“北”字碎银?徐祯和拿起碎银,与沈明月说的“南”字碎银拼在一起,正好是完整的一块,上面隐约能看出“忠”字的轮廓。
《女诫》里夹着张纸条,是二姑母的字迹,墨迹被泪水晕开了大半:
“祯和,别怪你姑父,他也是被兖王逼的。南记粮铺的地窖里,有你父亲当年留下的军械清单,还有……你娘的画像。二姑母对不住你,更对不住你娘,只能用这条命去赔了。”
徐祯和的手猛地一抖,碎银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她抓起匣子就往外跑,门房见她神色不对,连忙问:“小姐去哪?”
“去南记粮铺!不,去兖王府!”徐祯和的声音带着哭腔,她现在才明白,李大夫说的“容易走的路”,往往是用最痛的代价铺成的——二姑母要去的,根本不是赔罪,而是拼命。
夜色里,侯府的灯笼被风吹得剧烈摇晃,像在为这场迟来的救赎,发出绝望的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