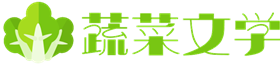洪武时空·南京城外
少年朱棣与徐妙云风尘仆仆赶至应天府。
“越靠近皇城,心里越不踏实。”朱棣攥紧缰绳。
徐妙云宽慰道:“殿下素来循规蹈矩,不必忧心。”
“但愿吧…”朱棣总觉脊背发凉。
御书房内,太监王景宏疾步禀报:“启禀皇上,燕王殿下与王妃候旨觐见!”
朱元璋合上奏折,”传燕王妃去坤宁宫陪皇后,让老四这混账在殿外跪着!”
“遵旨!”
王景宏退出御书房,高声宣道:”皇上口谕,燕王妃即刻前往坤宁宫侍奉皇后娘娘。”
“公公,本王呢?”朱棣急切追问,此刻唯有在马皇后身边才觉安心。
“燕王殿下,皇上命您在此跪候。”
朱棣与徐妙云面面相觑,不敢多言。徐妙云递了个眼色,匆匆往坤宁宫求援——这世上能劝住朱元璋的,唯有马皇后。
待批完奏章,朱元璋踱出御书房,见朱棣仍跪在阶下。他面色阴沉如铁,目光似刀。
朱棣心头猛颤,暗叫不好。
“儿臣叩见父皇!”他慌忙伏地行礼。
朱元璋一言不发,只居高临下盯着他。朱棣如卧针毡,冷汗涔涔。
“求父皇明示,儿臣所犯何罪?”朱棣强忍恐惧抬头。
“老四,能耐不小啊!”朱元璋突然蹲下身。
“儿臣实在不知……”
“好大的狗胆!竟敢谋反!”
炸雷般的怒喝惊得朱棣浑身剧颤:”冤枉!儿臣绝无此心!”
“还敢狡辩!”
朱棣脑中轰然——他素来忠心辅佐太子朱标,莫说行动,连谋逆的念头都未曾有过。在洪武朝 ** ?除非疯了!
“父皇明鉴!”
“咱还能诬赖你不成?”朱元璋虎目圆睁,”来人!把这逆子吊起来抽!”
二虎领着锦衣卫疾步而来。
“父皇开恩!儿臣冤枉啊!”朱棣的求饶声回荡在宫墙间……
东宫
小太监急报:”太子殿下,燕王夫妇入宫了,此刻正在御书房面圣。”
朱标霍然起身:”快备朝服!”
他最清楚父皇的脾气——老四要遭殃了。
得赶紧去救人。
……
坤宁宫
徐妙云来到病榻前,看见卧病的马皇后。
“儿臣给母后请安!”
马皇后微微颔首,”好孩子,到哀家身边来。”
她示意徐妙云坐在床沿。
“母后,燕王殿下恐有不测,求母后向父皇说情。”徐妙云虽不知详情,却察觉朱棣处境危急。
马皇后猛然想起此事,”玉儿,速备衣裳!即刻前往御书房!”
她深知朱元璋脾性,对其所思所想了然于心。
马皇后携玉儿与徐妙云匆匆赶往御书房。
“母后,究竟发生何事?”徐妙云仍不明就里,只知朱棣定是惹上祸事。
“此事说来话长,容后再细说。”马皇后一时难以道明。
临近御书房,她们遇见匆匆赶来的太子朱标。
众人抵达时,正见朱元璋已将朱棣悬于梁下。
朱元璋手持皮鞭立于侧,朱棣背上已现数道鞭痕。
“重八!”马皇后见状急忙喝止。
“父皇息怒!”朱标接过朱元璋手中皮鞭。
“父皇!儿臣冤枉啊!”朱棣仍在喊冤。
“快放老四下来!”马皇后心疼地吩咐。
二虎望向朱元璋,见其怒气渐消,这才奉命放下朱棣。
朱棣至今仍不知自己何时竟有谋逆之心。
“母后,儿臣绝无二心!”朱棣向马皇后申诉。
马皇后轻抚其背,”母后明白,母后都明白!”
“父皇,母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徐妙云追问。
此刻朱棣与徐妙云皆茫然不解,朱棣平白挨了顿鞭子。
“先前有人预言老四日后将谋逆登基。”马皇后解释道。
“何人如此诬陷?儿臣岂敢有此妄念?”朱棣倍感冤屈。
“此人自称来自六百年后,名唤萧然,知晓诸多秘辛。”朱标补充道。
“父皇母后竟信此等江湖术士?”朱棣几欲泣下。
朱元璋取出两张相片,”尔等且细看!”
朱棣疑惑接过,徐妙云凑近观瞧。
相片中一袭龙袍的老者虽年迈却威仪不凡。
二人凝视相中永乐帝容貌,竟觉莫名熟悉。
朱元璋指着相片,”可觉眼熟?这便是四十年后的老四。”
朱棣与徐妙云相顾骇然,此刻二人心绪大乱。
“父皇…儿臣冤枉啊!”小朱棣急得额头冒汗,却不知该如何辩解。
朱元璋冷哼一声:“咱打错你了?你这逆子还敢 ** 夺位!”
马皇后与朱标沉默不语,小朱棣和徐妙云也不敢出声反驳。这罪名听着荒唐,偏又无从辩驳。
“父皇,儿臣…”小朱棣张了张嘴,终究无言以对。
王景宏指挥太监搬来座椅,朱元璋扶着马皇后落座:“妹子,先歇会儿。”
待众人坐定,朱元璋开口道:“老大,你把前因后果给老四说清楚,让这混账知道萧然的事。”
“儿臣遵命。”朱标应声,随即讲述起萧然突然现身坤宁宫的经过,将事情原原本本道来。
听完这番离奇遭遇,小朱棣与徐妙云惊得说不出话。看着手中照片,小朱棣再不敢喊冤,转头望向仍在 ** 的徐妙云。
“母后,您的病…”小朱棣急切问道。
马皇后温声道:“那位先生说能治。”她更忧心的是朱标和朱雄英的安危。
“那大哥和雄英…”小朱棣连忙追问。
“应当无碍。”马皇后答道。
小朱棣长舒一口气,心知自己起兵皆因朱允炆削藩太甚。若大哥和雄英安好,这般祸事自然不会发生。
……
现代时空里,萧然和朱棣计算着时日。
“老爷子,差不多五天了。”
朱棣疑惑道:“见太祖高皇帝与这有何干系?”
“去了您就明白。”萧然笑着打量朱棣,“穿哪套衣裳去?”
虽然从大明带回不少衣物,但为适应现代生活,朱棣平日都穿便装。此刻他选了件绛红长袍:“既是回大明,自然要穿大明衣冠。”
“这身挺好,可别穿龙袍——我怕太祖高皇帝见了血压飙升。”萧然故意打趣,缓解朱棣的紧张。
“要不要备些见面礼?”
萧然指向角落的木匣:“早准备好了,保准太祖高皇帝满意。”
朱棣掀开匣盖,看见里头的红薯土豆,挑眉道:“你小子就送这个?”
“老爷子,此物在大明洪武年间尚未出现,红薯与土豆每亩可产数千斤,若能在当时推广种植,天下百姓便不会忍饥挨饿,粮食之忧将迎刃而解。”
朱棣身为 ** ,自然清楚亩产数千斤的分量。
“确是稀世珍宝,务必带上!”朱棣暗自欣喜。
这份厚礼别出心裁,定能讨得朱元璋欢心。
一切安排妥当后,萧然拱手道:“老爷子,时辰已到,我们启程吧。”
“好!”朱棣略显局促的神情被萧然尽收眼底,显然这位 ** 风云的 ** 此刻仍难掩忐忑。
……
恍惚间,萧然与朱棣已立于洪武十四年的南京城。
御书房门前,朱元璋与朱标同时抬头。
“来者何人?”二虎立即按刀厉喝。
朱标见萧然去而复返,眼中闪过喜色。
朱元璋早已等候多时,他迫切想向萧然求证马皇后与朱雄英的病情能否医治。
随着朱元璋摆手示意,二虎躬身退下。
老皇帝的目光越过萧然,径直落在其身旁的苍老身影上。
朱棣望着朱元璋展露笑颜,百感交集。
即便已是垂暮之年的永乐大帝,面对朱元璋时仍会本能地战栗——这是镌刻在血脉里的敬畏。
朱元璋凝视着那张与照片重合的面容。
“陛下!”萧然出声行礼。
朱棣轰然跪地:“父皇!”
虽现下朱元璋正值壮年,朱棣已是白发苍颜,却丝毫不显突兀。
朱元璋沉默地审视着朱棣。
一旁的朱标猛然醒悟来者身份。
“你……当真是老四?”朱元璋沉声发问。
“儿臣不孝,叩见父皇!”
见朱棣须发皆白,朱元璋胸中郁气稍缓,却仍冷着脸道:“平身吧。”
朱棣暗自苦笑。若父皇要责罚,方才已在小朱棣身上发泄过了——那孩子此刻正在坤宁宫敷药。
朱标上前搀扶朱棣。
望着长兄,朱棣眼眶发热:“大哥!”
朱标温润如初:“虽年华老去,雄姿犹在。”
王景宏搬来座椅,众人相继落座。
朱元璋的目光如炬,令朱棣如坐针毡。但瞥见身侧的朱标,他心下稍安——这位长兄带来的安全感,始终是诸位皇子最坚实的依靠。
【“先生,先前讲到允炆削藩之事,还请继续。”朱标适时打破凝滞的气氛。
永乐大帝与洪武大帝相对无言,四十年的岁月鸿沟让彼此显得格外生疏。
殿内陷入微妙的沉默。
“上次聊到哪了?”萧然揉了揉太阳穴,这些日子与朱棣讨论大明旧事太过频繁。
思绪有些纷乱。
“老十二遇害了!”提及此事,朱元璋眼中仍迸发着怒火。
那是对朱允炆的愤恨!
萧然瞥了眼身旁的永乐帝,觉得由当事人来讲述这段历史实在不妥。
朱棣会意,关于靖难之役的往事,他确实不便亲自向父皇禀明。
“父皇,儿臣想出去透透气。”
“景宏,陪着燕王。”朱元璋朝侍立一旁的王景宏抬了抬手。
“遵旨。”王景宏躬身引着朱棣退出大殿。
萧然整理思绪,缓缓道:”目睹其他藩王遭遇后,燕王殿下便佯装疯癫,暗中筹备起兵事宜。”
“区区燕王府亲兵,如何抗衡举国之师?”朱元璋百思不得其解。
“建文削藩期间,燕王已暗中布局。建文元年六月,千户倪谅告发燕王谋反,朝廷下令捉拿燕王府属官,都指挥张信却临阵倒戈。”
“同年七月,燕王以’清君侧’之名誓师起兵,史称靖难之役。这场叔侄对决持续了整整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