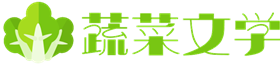北风从田埂的谷穗上掠过,带着露水与泥土的腥甜。天光方才像纸一样被人揭开一层,薄,湿,远处的城影淡得像不愿被提起的旧事。姜梨站在废祠外的槐树下,把小布囊再系紧了一道,手指在打结的最后一环上停了停,像在落一枚印。
凉生站在她侧后,目光顺着田埂往北,那里是一条被晨雾舔过的白线。两人对看一眼,他抬手,掌心向下,轻轻一压。
她回他同样的手势:走。
田埂边有水,水上浮着细细的蕨。脚下泥软,鞋帮上很快沾了两圈泥边。她不急,步子长短有度,像在按照某种记在心里的尺匀匀量着。凉生跟在半步之外,脚印落在她的脚印边,稍偏,像是故意给后来的人留出一条猜不准的路。
天更亮了一指。前头有一条小路与田埂相接,路边立一根斜倒的木牌,牌上残了几个字:“北……渡……碚”。“碚”字被虫咬了角,像笑又不像笑。她停住,回头望一眼南边的城。城在雾里,把一切人的声息都吞回去了。
她把手伸到凉生掌下,掌心向下,轻轻一压:避。
凉生点头。他从袖中摸出两条薄薄的麻带,递给她一条。两人俯身,把脚踝上露出的鞋纹用麻带缠了一圈,缠得不紧、不松。她还把携带的小布囊的外形调整了一点,把囊口压平,让它看起来像普通的饭团包。她的眼在这一刻更像是手,能把线与面都拢得很服帖。
远处忽有犬吠。不是村犬那种懒声,是短促,硬,连着三四下,像敲木的节。凉生眼里微一紧,回头。田埂尽头,有四五个身影从雾里走出来,穿短褙子,肩上挎着弓,腰下挂短刀,走得有章有法。为首那人背脊很直,步子落地先脚尖后脚跟,像经过训练。姜梨收回视线,抿唇。
她掌心向下,轻轻一压:换。
凉生明白。两人交换了位置,姜梨微微落后半步,像是随行的小妹,凉生则把身姿放得更寡淡,眼神收束得一丝不散,肩略垂,让肌肉的线条隐在褙子布纹里。
那几人很快逼近。为首者喝道:“停!何人,哪乡,去往何处!”
姜梨抬眼,目色不躲:“南巷榆树旁姜家,去北渡小集买药材。”
“买何物?”
“紫苏、半夏、艾叶。换香草,避湿。”她答得干净,不多说一个字。
为首者目光在她身上扫过,又扫凉生,落在他手腕上那一圈旧伤上,略停。那停顿像一粒灰落在桌上,肉眼能见,却不能说。旁有一名少年把鼻子凑近嗅了一下,皱眉:“一股怪香……像栀子,又不像。”
姜梨道:“衣里夹了栀子衣。避虫。”
少年“哦”了一声,又像故意,伸手要去掀凉生的袖口:“把袖抬起。”
凉生不动。姜梨侧身一步,挡在他与少年之间,动作不陡,像是顺手,却恰好挡住了那只手。她抬指指田埂尽头的浅沟:“小心。昨夜雨,边上泥下去半寸。你鞋底花浅,落进去不好拔。”
少年哼了一声,不信。一脚就踏下去,果然滑。他“哎呀”一声,手忙脚乱往外拔,拔得鞋带都松了。“别动!”为首者低喝,伸手去拉,脚也探到沟边,把将落未落的势压住。
这一小乱,打断了原本搜检的节。姜梨乘势从怀里摸出一张小纸,双手奉上:“大人,里正的回条。说南巷人等可随出城一带采药,勿误县里捕务。”
为首者接过,扫了一眼。纸上用很平的楷字写着几行,末尾有里正小印。他看印,印泥干了两日的色,字口边沿有轻细的毛口——像是用过、就手的惯常章,并非急就的假物。他“嗯”了一声,把纸折回,视线仍不离凉生:“这位是你什么人?”
“表弟。口拙。”
凉生垂眼,像不通人事的木头。他手心向下,轻轻一压。
姜梨心安了一寸。为首者收回目光,道:“近来查诏逆案残党,你们靠道走,别入林。有人问话,按里正回条答。若有不便处,回南巷里正处报。”
“谨记。”
那几人让出道。少年还在挤鞋,脾气上来:“麻烦!一身泥!”为首者斜他一眼,少年不敢再嚷。
走出十丈,姜梨才把气落下。她低声道:“刚才印角若被他多看一眼,能挑出三处不同。”
凉生侧目。她也不藏,道:“里正印旧,印角磨得圆。这个是我前日替他把印角补了点粉,磨过一次,边上有新旧两色交界。第二,回条用的纸是祠里经折的剩纸,纸筋杂。第三,字是我代写,里正三画一笔常有抖,我学不到。但你袖里那条线若落出一寸,谁都能抓住。”
凉生抬手,掌心向下,轻轻一压:对不起。
姜梨摇头:不。
再往北,路渐开阔。有一条小溪斜斜横在前面,溪上是一座窄木桥。桥那头聚着几个人,担箩筐、推车,像要过桥又不敢。近前一看,才知桥板中间断了一条缝,缝不宽,刚好卡住小车轮。一个商人打扮的汉子在发愁,额头上汗珠一颗颗,账房似的小子抱着簿,眼睛却四下看,像担心的不只是桥。
姜梨上前,道:“要不要借力?”
那汉子抬头,见来的是个女子,愣了一下忙笑:“借!借!姑娘这边请,若能过了桥,给你们搭个顺风车如何?往北集,我一车粗布、一车盐包。你们要去那边?”
“正是。”
姜梨看一眼桥板,蹲下用指节敲了敲断缝两侧的木纹,木纹年头不少,近心处还紧。她转头对凉生:“把车头抬半寸。”凉生点,手像无骨一样轻轻托起,托得毫不吃力。她掏出前晚在角门处折下的半截竹钉,试着塞进缝里两块板之间的咬合处。竹钉软硬适中,塞进去时发出一声极小的“唧”。
“再往右一指。”她低声。凉生微移。车轮从竹钉上滑过去,像踩过一条看不见的桥。
商人连声道谢:“巧手巧手!真是巧手!敢问两位如何称呼?”
“姓姜。”她笑笑,“这位表弟,姓凉。”
“凉家的小哥,力气好!”汉子笑得见牙,“我是王恒,跑南北线,常去北渡,再北上到州府。两位要去州府?我们可以一路。”
姜梨眼底掠过一点思量。她需要的是借道、人群,以及名义。她点头:“借王掌柜的顺风。只是路上若有人查,我们便搭你车,说是替你看伤病的短工。”
王恒愣一瞬,随即大喜:“求之不得!我们昨夜有个伙计崴了脚,还唉声叹气呢。”
车队挪上桥,咕噜咕噜地过了溪。桥头草丛里起了两只野鸡,扑棱飞起,把一阵草籽撒在路上。姜梨一手按了按头发,把一缕掉在额角的发尾抿进鬓边。凉生在人群旁走,目光不显山不露水,落在最容易忽略的地方:车轮印、鞋底纹、盐包口的封绳。
盐包用的绳子是粗麻,齿距不齐,但每隔三指就有一个小结,那是熟练工的手惯。粗布卷上印了“东源”的小戳,戳上边缘糊了点浆糊,浆糊新。账房小子抱的簿页是绵纸,左下角沾到过香灰。凉生看这些,看得像他在看一张风的路。他抬手,掌心向下,轻轻一压:可信。
姜梨点头。
王恒把两人安在第二辆车旁。车上放的是几只水桶,桶箍有老裂,她用指背轻轻敲了敲,发出声色带哑的响。她掀起桶盖,闻到一股淡淡的铁味与木气,笑道:“桶要换箍。今晚找个铁匠。”
王恒啧啧:“姑娘一眼便知。路上有你,心都定了。”
到了巳时前后,路上尘起得高些。一处路亭前,立着一面破旗,上写“巡”。亭下有三五名公差样的人影,旁边还有两匹马。那马眼亮,鞍具齐整,马蹄新钉,显然是自城里刚出的。王恒压低声音:“娘的,鹰犬。”
姜梨把篷布抬了一指,往外看。那几人的帽檐压得低,身上罩着看似平常的褙子,褙子袖口却用的是窄边的黑布滚边,滚边的针脚密而直,多了一种不该有的齐整。一个较高者背着手走来走去,鞋后跟有极轻的铆声。她心里沉下一颗沙。
她把手摸进布囊,摸到一个细瓷瓶。瓶里是她昨夜配的艾叶粉、麝香末,混了极淡的硫磺。她用指尖粘了极少,揉在篷布内侧的木梁上。那香很轻,轻到闻不出来,只是会让靠近的人下意识皱一次鼻。
她掌心向下,轻轻一压:掩。
凉生明白。他把身上的褙子领口掩到更高,像个不喜言语又怕风寒的小伙计。姜梨则从布囊底摸出一张写着“药单”的纸,纸角折了三个小角——三角,第三个角半折,象征“否”,是她与凉生之前定下的暗记:“有人问药,三折为否,言少,多咳。”
轮到王恒的车。那高个儿一抬手,冷声:“停。何人,去向何处。”
王恒陪笑:“官爷消暑。我是王恒,跑南北线。去北渡,送几包粗布盐。”
“车上何物?”
“水桶,药包。”王恒眼珠一转,语气里添了半分担心,“大人,前日北面的村子起了湿瘟,说是水沟里有脏东西。我们这几日往那边送盐,都用艾草隔着。姑娘——”他一抬手,把姜梨“请”了出来,“这是行路看病的,替我们挑药。”
那高个儿把视线移到姜梨脸上,眼里掠过一丝不耐:“何医?”
“不敢称医。”姜梨把药单递过去,“都是避湿、安胃的粗方。”她轻咳两声,不重,像有习惯性的咽喉微敏。高个儿皱了一下鼻,果然向后收了一寸。他接过药单,扫了一眼——纸上字与里正回条不同,笔意更拘谨,像是刻意写成“药行小字”。右下角盖了一个“仁和”的小戳,戳泥新,边口干净。
“开给谁?”
“王掌柜。”姜梨低声。
高个儿把药单往后一抛:“开箱。”
两个小差动手掀篷。篷下的药包裹得规整,上头铺了一层艾草。小差伸手翻了一下,手背上立刻起了两点小红疹——艾草粉混着极淡的麝香末,本无害,只激一点表皮敏感。小差下意识把手往袖子里一缩,嫌恶之色一闪。高个儿脚跟一顿,正要再细看,忽然外头一阵马蹄声急,另一个持旗的从官道那边奔来,气未匀:“齐头!北城方向送来的文书到了!”
高个儿接过,扫两眼,脸色敛起几分肃:“查诏逆案残党,重点盯南巷与库子出入人员。凡同行商队,若有南巷口音者,逐一比对。”
他抬眼,又落在王恒与姜梨脸上。王恒笑意一滞,喉结滚了滚。姜梨心口那条弦被拨了一下,极快地压住。
她咳了一声,示意身后的凉生把水桶推近来:“大人若不嫌弃,可先用此水洗手。我们怕惹湿瘟,一路烧开备用。”
高个儿冷笑:“湿瘟能怕出官路?”却还是把目光往水桶里一扫。水面干净,桶箍虽旧,但箍缝间她早用松香泥补过,颜色与木色相近。高个儿伸手抄起半瓢水,甩在地上,泥上立刻起了潮痕。痕边像有一圈极细的波。他的视线在那圈波上停了半息,转开。
“说话。”他忽地抬声,指向凉生,“你是哪乡口音?”
凉生抬眼,目光平,唇动了一下,发出一个模糊的音:“……北。”声音沙,有点像喉咙磨过碎石。
高个儿皱眉:“他喉有病?”
姜梨低头,指着药单上其中一味:“半夏。”
“病几时?”
“两年。”
高个儿盯她,像要从她的眸里抠出一句谎。姜梨把眼神放得更沉一点,像落进水里的一粒小石。
片刻,他收回目光,挥手:“放行。”
车队过亭。王恒长长吐出一口气,笑却没笑出来:“娘的,今日的日头一点都不热,我的后背全是汗。”
姜梨把药单收回,折角再压紧一线。她对凉生露出没声的笑。他掌心向下,轻轻一压:险。
她回他:过。
午后,路转入一道宽一些的官道。道旁是柳树,叶子长又软,风一吹像在道上铺了一层绿絮。远处的云压得低,日头像在云后头喘气,透出来的光有些疲累。王恒的车队走在中间,前后各有一辆小商贩,挑着鸡笼、果篮,构成一条看似平常的流。
走到一个水歇的地方,大家把车靠到一边,歇脚吃干粮。王恒把一块饼掰了半块给姜梨,再塞一块给凉生。凉生不接,她接了,递给他。他本可以直接接她的手,却微微绕了一下,从她手掌下方取过,像绕开一阵风。两人之间的那一点礼数,像一条挑得很细的线,紧、却不勒。
“你们真是做药的?”王恒啃着饼,有些好奇又有些试探。
“我父亲是。如今只会些粗。”姜梨答,眼神没有防备,也没有逾矩的交情,好像把话摆在桌上,任你看,也不过如此。
王恒“哦”了一声,抹一把汗:“那正好,晚上看看小刘的脚。扭得不轻。再往北,大概三天能到州府,路上有个镇子,叫‘驿柳’,客栈还行。你们要能到那儿,就可以换一趟更稳妥的车,跟我们一起进州。”他说到“州”的时候,压低了声,“州里近来查得紧,据说是宫里催的。”
姜梨应声:“知道。”
凉生吃东西慢。他看着不远处一个挑鸡笼的老人,鸡在笼里被日头晒得半死不活,舌头伸出来像一条薄薄的红叶。老人时不时往鸡身上洒点水,嘴里说:“活着,活着才值钱。”凉生看了半天,忽然垂眼,把那半块饼很认真地分了一片,递给姜梨。她愣一下,随即接过。那片饼很小,像他从他自己的“值钱”里抠了一指给她。
她指尖碰到了他的指节。他的手冷,冷得像夜里水槽内壁。他抬眼看她,眼里不问,也不说。她掌心向下,轻轻一压:谢。
傍晚,天边揉了一团暗色的云,像谁用指腹把墨抹开了。小小的风从水面上涌过来,带着潮气。车队找了一处背风的小坡扎了夜。王恒让伙计去拾柴,有人去河边挑水。姜梨蹲在车尾,翻自己的布囊。她把那半枚玉坠拿出来,放在手心里。玉坠温度不冷,背面的纹理在黄昏里像一条很旧很浅的路。
她从布囊底又摸出一张薄薄的纸,上面拓着前日她在祠里搓下的一段龙纹。她把玉背与拓纹对齐,断口处与龙鳞的某一块刚好在一处。她的心轻轻动了一下,又稳住。她拿出炭条,在玉背的一处最不起眼的角落点了一个极小的点。她对凉生比了个手势:记。
凉生颔首。他的目光落在她指下的拓纹上,停了许久。他的眼神像是站在一个门外,看一个屋里的人把箱子一道一道地开。他伸手,指腹在“龙”的某一笔上极轻地一抹,眉心极浅地动了一动。姜梨看到了,没问。她知道,有些问,问出来就碎。
夜里,火堆点起来,烟往上走,带着艾草的清苦。王恒过来,挠头:“小刘的脚——”
姜梨让他坐下,解了小刘的鞋。踝处已经肿起,她手掌按上去,力道不重不轻,小刘“嘶”的一声。她笑一笑:“疼才知道是自己的脚。”众人笑了一阵,气也松一阵。
她拿出一包药,里头是她午间捣的艾、姜、盐、栀子皮混末,以麻布包敷,外头又用一条薄绢缠住。她边缠边说:“明日不要贪快,车走慢点,十里停一次。你们嘴上嫌慢,脚下会谢你。”王恒连连点头,把嘴里的“慢”全吞下去。
夜更深一点,火星在黑里一颗一颗跳,像极小的眼睛。人都散了,各自去车边、草里、树根边睡。姜梨靠着一只水桶坐,凉生在她身侧不远,背靠车轮。两人之间的距离刚好,近了,响;远了,冷。
“你……”她开口,又停。她不问“你是谁”,那句问像一条针,扎下去,拔不出来。
凉生看她一眼,慢慢把右手抬起来,掌心向下,轻轻一压:在。
她笑了一下,很轻。“我小时候,爹带我走过这条路。那时他给我讲水的道理,说水要绕,要贴着边走,别急。”她声音像在给火堆里的木头讲故事,“后来他不在了,我就照着他讲的走。绕的时候会急,急也绕。”
凉生没有看火。他看她。夜里的她,眼睛像一汪水,水底有石,石在。他抬手,指尖在地上点了一下,点出一个点,又在旁边点了一个,再在两点之间挪了挪指腹,似乎要把两点连起来。他掌心向下,轻轻一压:跟。
她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好。
她把布囊里最底的薄本翻出来,那是她父留下的“杂识”,纸边起毛,字里有酒气与药气混出的旧味。她把今日的见写下来:细齿绳、斜磨铜片、官道亭、“巡”旗、滚边黑布、铆钉马蹄、仁和小戳、印角新旧、艾粉麝香、湿瘟借口。她写得很小,像怕把纸写痛了。
她又写:北上。州。宫市在前。避、藏、借。
写到“借”时,她停了一下。她抬眼去看凉生。凉生看着她。她忽然露出一个带点自嘲的笑:“借你的命。”
凉生摇头。他把手掌按在地上,掌心向下,轻轻一压,然后很慢很慢地抬起,像托起一样。意思很明:给。
她喉咙一紧。她把布本合上,压在手心里,像压住什么要涨上来的东西。很久以后,她低低道:“到了州里,我们先去‘驿柳’。那里的客栈掌柜姓蒋,认识我爹。他不一定记得我,但我记得柜台角那枚豁口。”
凉生点头。他掌心向下,轻轻一压:走。
第二日一早,车队起行。一路到午,都平平。午后近申,天边的暗云终于沉到了头顶,雨从冷里落下来,先是细线,再是密帘。王恒骂了一句,叫伙计把篷布压低。路上一片潦,车辙里积了水,水面被车轮搅成一层层扇形的纹。
雨中他们又遇到一处简陋的关卡,木杆横,绳搭在柱上。两名差役躲在棚下,身上湿得半干半湿。棚下还站着两名穿青褙子的陌生人,腰间没有佩刀,但站姿很稳。姜梨看了一眼那陌生人的裤脚——裤脚缝线略高于常人一指,线脚收得干净,像是北地营里出来的人。她心里又落了一枚石。
这一次的盘查比午前更细。他们让每个人报乡里,报去处,还要打开一半盐包、粗布卷检查。王恒额头上全是雨,嘴里“是是是”。轮到凉生,果然又有一只手伸了过来,要掀他的袖。
姜梨抢前半步,把一个包递给差役:“这是止咳丸。雨里辛苦,官爷嚼一粒,热气从胸口上到鼻,一会儿便好受些。”她说话时眼不看凉生,像这袖从来不是她要挡的。
差役犹豫了一下,正要接,那青褙子的人冷声:“别吃。拿过来。”把包拿过去,指尖一捻,掰开一粒,凑鼻闻。丸里有半夏、桔梗、苏叶,都是寻常解表;外裹极薄的一层糖粉,糖是粗糖,颗粒不匀。他点点头,眼神却没缓,反更冷了一分。他抬眼看姜梨:“你师承何处?”
“乡里。”
“乡里何人?”
“父。”
“父何名?”
姜梨沉了一下,答:“姜九。”
青褙子的人目光在她脸上停了片刻,移开,低声与同伴交换了两个字:“记名。”
雨把他们的声音打碎。木杆抬起一寸,又落下。两名青褙子的人一左一右站开,像两片叶,叶背上全是水。
就在这时,后面一辆鸡笼车里的鸡突然乱扑,笼子一倒,鸡羽飞得满天。鸡笼与盐包撞在一起,盐包的麻绳“嘣”的一声崩了一股。王恒大叫:“别别别——盐!”众人一阵乱拾。差役与青褙子的人都被这乱撞了视线,往后一看。
凉生的手在此刻极轻地动了一下——只是把袖口向里扣了半指,扣住了那只旧伤疤最醒目的一角。他的动作在雨里像一滴水,落地就没了。
姜梨在乱中把一枚小小的竹片塞进盐包绳结里,竹片被盐水一泡,立即膨起一丝,绳结就好系了。王恒大叫“妙!”又自己踹了自己一下“娘的,手漏!”
青褙子的人回过头来,目光扫过,像一把冷刀从每个人脸上刮一遍,落在凉生手背上时只停了不到半个呼吸。那一停没逗留,像他眼底另有事更重。
木杆终于抬了,车队从雨里慢慢走过去。雨在篷布上打,打出一行行小鼓点。
到了黄昏,雨停了,云像被人从中劈开,露出一缝土黄的天。王恒说:“再走半个时辰,就到‘驿柳’。”
姜梨把手伸出篷布,接了一滴刚落下的水,水凉,把她掌心的热压了下去。她把半枚玉坠在袖里摸了一下,像摸一块会发光的石。
凉生看她。他抬手,掌心向下,轻轻一压:累?
她摇头:不。
又一压:怕?
她想了想,点了一下,又摇了一下:怕,也不怕。
他低低嗯了一声。那声嗯轻得像风吹过草尖。
夜里,他们进了“驿柳”。镇子不大,客栈两层,门口挂着一盏油灯,灯沿有一圈黑。掌柜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面白手快。姜梨在柜台前站了一瞬,目光落在柜台角那枚豁口上。豁口真在,她心里那根弦有一处松。
“掌柜,”她笑,“打尖住店,两间朝里,一晚。”
掌柜抬眼:“几位?”
“两位。同行客商。”她把王恒叫过来。王恒跟掌柜一阵熟话,递了牌子与押金。掌柜把牌子一晃:“二楼东头。井在后。今儿炖的是鲫鱼,汤里放了姜丝和胡椒。”
“借福。”姜梨说。
入了房,她才真正把背上的气卸下半截。她把布囊放在案上,门闩挂好,把靠门的那只椅子腿往门边挪半指,椅脚与门缝之间留一个她能听见的“牙”。窗下栀子香没有,这里有的是木头潮气。她把半枚玉坠放在枕下,像把心放在一块不容易被看见的地方。
凉生坐在床沿,不动。夜里的客栈有一种与家不同的响:楼板的吱呀,人走廊里的脚步,厨下刀碰案的“当”。他把这些声都收进耳朵里,像把散在地上的线一根一根捡起来。
她走过去,在他面前坐下。她把手伸出来,掌心向下,轻轻一压:说。
他抬眼,眼底有一层很淡的光,像雨过后的水面。很久,他抬起自己的手,握住她的,掌心向下,轻轻一压,然后放开。他的唇动了动,极轻,像两个字轻轻落在木头上:“不走。”
她愣住。她不是没以为他会一直跟,但他在此时此地、用这两个字把那件事变成了不可更改,她胸口像被一只手压了一下,压出一口热气,又冷。
她点头:好。
她低声:“我去京,是要找东西:半玉的另一半,父亲书里缺的一页,还有……还有那件‘旧制’的影。”她不说“皇”,不说“龙”,她把那些字都放在“影”里面。
凉生的目光在“影”这个字上停住,呼吸很轻地乱了一下,又稳住。他点头,掌心向下,轻轻一压:帮。
她笑了。“你呢?要什么?”
他不答。他看着她,像看着水里一个人的影。他抬手,在案上用指尖点了三下:一、二、三。再把手按平,掌心向下,轻轻一压:你。
她想笑,又觉得鼻子酸。她“嗯”了一声,像是答应了一个不太敢答应的约。
夜更深,风从廊下过,吹得灯焰一跳一跳。她把那本“杂识”又翻开,写:驿柳,柜口豁。王恒可借。青褙子营线。雨中关卡。丸验。袖危。鸡解。得过。
又写:心愿——京。查旧制,寻内符。生……不走。
月光落在窗纸上,像一枚被揉皱又摊平的银票。她把笔放下,伏在案上,闭了眼。她听见隔壁有人打鼾,楼下有人笑骂,院里有猫在叫。她又听见自己心里有一口水,很慢,很慢地往下沉,沉到一个她看不见的地方,沉住了。
清晨,鸡未叫,客栈后有脚步轻轻过。凉生睁眼,没有动。他听那脚步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像是在数房门。脚步停在他们门外,门缝里进了一线风。他抬手,掌心向下,轻轻一压。姜梨醒了,坐起,眼里立刻有光,有锋。她从枕下摸出半枚玉,移到胸口一侧,像把一块石搬到另一个不容易被碰的地方。她把指头伸到门闩处,轻轻一勾。椅脚与门缝之间那一点“牙”发了一声极轻的“叩”。门外的脚步顿了一顿,又走了。
两人都不说话。风把窗纸吹得鼓起又贴回,像一张胸在呼吸。
天亮时,王恒来敲门:“走咧——”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刻意的明亮,像怕把夜里什么东西压下来。
姜梨开门,笑:“小刘的脚?”
“好多了!”王恒笑,“姑娘手真好。我晚上做梦都在谢。”他笑着,眼角却扫了一下屋里的陈设。姜梨看见,笑意不变,心里却在本上写了一笔:王恒——人厚,心细。
凉生在门后,把手掌按在门框上,掌心向下,轻轻一压:谨。
她点:谨。
下楼时,她看了一眼柜台角的豁口。豁口边有一条很浅的刻痕,是“九”字的一半,像有人曾经把一个名字刻到一半就停了。她指尖在那痕上轻轻一按,像按在很久以前的一个下午。掌柜从内出来,笑:“昨夜睡得可好?”
“好。”她笑,“鲫鱼汤好。”
“常来。”
“会。”
掌柜眼里闪过一点认不出的东西,像一只鱼在水下翻了个身,又沉下去。
他们出门,天清了,云被风扫得很高。王恒的车队在门口等,马打着响鼻。王恒拍了拍第一辆车的车板:“上吧。半日到州门。州门前要再查一遍,比昨日更细。你们两位……”他又压低声音,“若不稳,就先走后门,绕柳堤。那边有条旧道,走的人少。”
姜梨点。她把手伸给凉生,掌心向下,轻轻一压:今日,稳。
凉生回她,掌心向下,轻轻一压:稳。
车轮碾过青石,发出一种与土路不同的声。她把窗帘掀了一指,远处的州城高了起来,城门上的“州”字被日光照得白亮。她把那半枚玉按在胸口,像把半个心按回去。她知道,前面还有关、还有查、还有人、还有“影”。但她也知道,她与他,已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