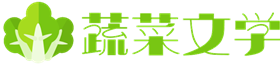简介
历史脑洞小说《逆天命:元清明》是最近很多书迷都在追读的,小说以主人公无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天涯沦落人001作者大大更新很给力,目前连载,《逆天命:元清明》小说124308字,喜欢看历史脑洞小说的宝宝们快来。
逆天命:元清明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 《逆天命》第十四章:元军粮饷·被将领倒卖至黑市
至正十一年四月十五,河南戍军的粮饷车抵达汝宁卫时,车辙里的泥水还带着黄河的腥气。哨兵赵二狗扒着营门的木栏,盯着那二十辆马车——车帘被风掀起的瞬间,他看见麻袋里露出的不是糙米,是掺了半袋沙土的谷糠,谷糠里还混着几粒发霉的豆。
“别盼了。”老兵王二柱往他手里塞了块硬得像石头的麦饼,饼边沾着草屑,“这个月的粮饷,估摸着又是这样。张百户昨儿去领粮,回来就把自己的甲胄当给黑市了——换了三升小米,够他婆娘和娃吃两天。”
赵二狗咬了口麦饼,沙砾硌得牙床疼。这是他从军的第三年,第一年还能领到掺三成沙的糙米,第二年是谷糠,今年连谷糠都掺了沙土。他摸了摸腰间的环刀,刀鞘上的漆早就掉光了,露出的铁面生着锈——上个月有个兵痞想抢他的刀去换酒,被他用刀柄砸破了头。
“听说了吗?”赵二狗往粮饷车的方向努了努嘴,“押送粮饷的是李千总的小舅子,上回他把一半军粮拉去黑市,换了匹西域的宝马,李千总连眼皮都没眨。”
王二柱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唾沫里带着血丝——他的牙龈因为长期吃谷糠发炎了。“咱这汝宁卫,早就成了李千总的私产。粮饷、兵器、甚至咱们的军饷,只要能换钱的,他都敢卖。上个月有个新兵去告他,结果被安了个‘通红巾军’的罪名,活活打死在营门外。”
粮饷车停在中军帐前,李千总的小舅子刘三跳下车,腰间的玉佩撞得叮当响。他根本没去粮仓,反倒让士兵把麻袋卸进了自己的私帐——那里藏着杆秤,是用来给粮饷“掺沙称重”的。
“都排队领粮!”刘三扯着嗓子喊,手里的鞭子抽在粮车的木板上,“每人一斗,少废话!谁要是敢挑拣,这个月的粮饷就别领了!”
士兵们慢慢排起队,队伍像条病蛇,弯弯曲曲地绕着营房。有个刚从军的少年兵,手里攥着个粗布袋,袋角绣着朵歪歪扭扭的花——是他娘绣的。“刘爷,能多给点吗?我娘病了,等着小米熬粥。”
刘三的鞭子抽在他脸上,血立刻渗了出来。“你娘病了关我屁事?”他踹了少年兵一脚,“再敢多嘴,就把你这破袋子当柴烧!”
少年兵的布袋掉在地上,袋口散开,露出里面的几块观音土——他早就料到领不到像样的粮,从家里带了土来。赵二狗想上前,却被王二柱拉住:“别管,这世道,管好自己就不错了。”
轮到赵二狗领粮时,他看着刘三用个小斗舀谷糠,斗沿还故意刮得很平,一斗实际只有八升。“刘爷,这不够数啊。”他忍不住说。
刘三冷笑一声,往他的粮袋里又撒了把沙土:“现在够了吧?再啰嗦,我让你连沙土都领不到。”
赵二狗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他想起去年回家探亲时,爹把家里最后一只鸡杀了,让他带回来给长官“打点”,可他连像样的粮饷都没领到。爹的腿在修堤时被砸断了,全靠娘纺线换点药,要是这个月再没粮寄回去,娘怕是撑不住了。
领完粮,士兵们三三两两地往营房走。有人把谷糠倒进锅里,加水煮成糊糊;有人坐在墙角,用石头砸开麦饼硬壳;还有人抱着粮袋发呆——那点谷糠,够一个人吃五天,要是家里有老小,连三天都撑不过。
赵二狗刚走进营房,就看见张百户在打包行李。他的甲胄没了,只穿着件单衣,腰间捆着个布包。“百户,你要去哪?”
张百户把个小陶罐塞进他手里,罐里是半罐小米:“给你娘寄回去。我去淮西投奔红巾军——有个逃兵从那边回来,说红巾军管饭,还发新甲胄,不像咱们这儿,连狗都不如。”
赵二狗的手一抖,小米撒了些在地上。“投奔红巾军?那是反贼啊!”
“反贼又咋了?”张百户的声音突然拔高,“反贼至少给粮吃!咱们守着这破营,吃着沙土谷糠,替李千总卖命,最后还不是饿死、打死的命?我听说红巾军在徐州开了官仓,百姓都能吃饱,咱们去了,至少能当个有饭吃的兵!”
营房里的士兵都安静下来,有人摸了摸自己的粮袋,有人看着张百户的背影,眼里的光像被风吹动的火星。王二柱叹了口气:“张百户说得对。上个月我去黑市,看见李千总的人在卖咱们的军粮,一斗糙米换两匹丝绸,买粮的是江南来的盐商——他们用这些粮去黄泛区换流民子女,再卖给密宗寺院当祭品。”
赵二狗的喉咙像被堵住了。他想起那些粮饷车里的谷糠,想起少年兵掉在地上的观音土,想起娘纺线时佝偻的背。他突然抓起自己的环刀,往营外走:“我去黑市。”
“你去干啥?”王二柱拉住他。
“把我的刀当了,换点小米。”赵二狗的声音发颤,“就算当反贼,也得先让我娘活下去。”
汝宁卫的黑市藏在营外的破庙里,庙门挂着块“土地庙”的旧匾,匾后藏着个暗门,里面挤满了商贩、兵痞和偷偷来换粮的百姓。赵二狗刚走进暗门,就被个穿绸衫的商人拦住:“这位军爷,有啥好东西?甲胄、兵器、甚至兵符,我都收。”
商人的手指上戴着个玉扳指,扳指上的血丝还没擦干净——赵二狗认得,那是上个月被打死的新兵的,新兵的爹是个玉匠,这扳指是他给儿子的成年礼。
“我有把刀。”赵二狗解开刀鞘,环刀的寒光在油灯下闪了闪。
商人掂量着刀,又看了看赵二狗:“这刀是好刀,可惜锈了。最多换两升小米,或者一匹粗布。”
“两升?”赵二狗攥紧了刀柄,“这刀能劈铁!”
“现在是乱世,刀再多,不如一碗米金贵。”商人指了指角落里的麻袋,“看见没?那是李千总刚送来的军粮,一斗糙米换五匹丝绸,我转手就能卖给江南盐商,换十斗的价钱。你这刀,换两升算给你面子了。”
赵二狗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麻袋上印着“汝宁卫军粮”的字样,袋口露出的糙米饱满干净——这才是本该发给他们的粮饷。他突然明白,不是没有粮,是粮被他们自己人卖了;不是命贱,是这世道容不下他们这些想活命的兵。
“我不换了。”他把刀插回鞘里,转身就走。
商人在他身后骂:“傻当兵的!等你娘饿死了,看你还能不能抱着刀哭!”
赵二狗的脚步顿了顿,却没回头。他往黑市深处走,那里有个卖药的老婆婆,是他同乡,偶尔会偷偷给他留些草药。老婆婆的摊子前围着几个伤兵,有的胳膊被打断了,有的腿上生了疮——都是被军官打的,或者是因为饿极了抢粮被兵丁伤的。
“二狗?”老婆婆往他手里塞了个油纸包,里面是几块晒干的红薯干,“你娘托人带信来,说她还好,让你别惦记。这红薯干是她自己晒的,让我转交给你。”
赵二狗咬了口红薯干,甜味混着咸味在嘴里散开——那是娘的味道。他突然想起张百户的话,想起黑市麻袋里的军粮,想起少年兵脸上的血。
“婆婆,红巾军……真的在淮西吗?”他问。
老婆婆往四周看了看,压低声音:“前几日有个红巾军的信使路过,说他们在宿州杀了李千总的表哥——就是那个在黑市倒卖军粮的王掌柜。红巾军说,只要是被官军欺负的,他们都收,不管是兵还是百姓。”
她从怀里掏出块红布,塞进赵二狗手里:“这是信使给的,说要是遇到难处,就往南走,看见戴红巾的人,把这布给他们看,他们会帮你。”
红布粗糙的边缘蹭着赵二狗的手心,像团火。他把红布塞进怀里,贴着心口,那里还留着红薯干的余温。
回到营房时,王二柱正和几个士兵聚在角落里,地上摊着张从李千总私帐偷来的账册。账册上记着:“四月军粮:糙米五千石,实发谷糠一千石,余四千石售予江南盐商,得银五百两;甲胄百副,售予辽东部落,得马五十匹……”
“这狗东西!”一个士兵一拳砸在地上,“咱们在这儿啃谷糠,他用咱们的粮换银子、换马!”
“要不,咱们反了吧?”少年兵突然说,他的脸上还有鞭伤,却睁大眼睛,“去投奔红巾军,总比在这儿等死强!”
赵二狗看着少年兵,又看了看账册,突然从怀里掏出那块红布:“我知道红巾军在哪。”
士兵们围过来,看着红布,眼里的光越来越亮。王二柱把账册撕成碎片,塞进灶膛里:“今晚三更,咱们去粮仓——能抢多少粮就抢多少,然后往南走。愿意去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就当没见过我们。”
三更时分,赵二狗带着十个士兵,摸向粮仓。粮仓的守卫是李千总的亲信,可他们早就被收买了——守卫的家人也在挨饿,李千总连他们的粮饷都克扣。
“快点!”守卫打开粮仓的门,压低声音,“李千总今晚在营里宴客,喝多了,一时半会儿醒不了。”
粮仓里堆着二十几麻袋糙米,麻袋上还印着“军粮”的字样。赵二狗抓起一把糙米,饱满的米粒在手里滚,带着新米的清香——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摸到没掺沙的粮。
“装!”王二柱喊了一声,士兵们立刻用布袋装粮,动作快得像偷粮的老鼠,却没人觉得丢人。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远处传来马蹄声。是李千总带着亲兵来了,他大概是宴客时喝多了,想来看一眼自己的“私产”。
“有埋伏!”赵二狗把一袋糙米塞给少年兵,“你们先走,我和王大哥断后!”
少年兵想留下,却被王二柱推了出去:“快走!把粮送到红巾军那里,告诉他们,汝宁卫还有想活命的兵!”
赵二狗和王二柱举起环刀,冲向李千总的亲兵。他们的刀没亲兵的锋利,甲胄没亲兵的结实,可他们眼里的光,比亲兵的刀还亮。
“反了!你们这群反贼!”李千总在马上嘶吼,手里的弓箭对准了赵二狗。
赵二狗没躲,他知道自己躲不过。他只是用尽全身力气,把手里的环刀扔向李千总——刀没射中,却把李千总的玉佩打落在地,摔成了两半。
箭射中了赵二狗的胸口,他倒在粮仓的麻袋旁,嘴角却带着笑。他看见王二柱还在拼杀,看见少年兵带着粮袋消失在夜色里,看见粮仓的火把映着“军粮”的字样,像烧红的烙铁。
他最后摸了摸怀里的红布,红布上沾着他的血,像朵开在糙米堆里的花。他想起娘的红薯干,想起张百户的话,想起黑市商人的玉扳指——他知道,自己没白死,至少那些粮能送到该去的地方,至少还有人能带着他们的希望,找到真正能吃饱饭的军营。
王二柱最终也没能冲出重围,他被亲兵砍倒在赵二狗身边,手里还攥着半袋糙米。李千总看着满地的尸体和被抢走的粮,气得把弓箭摔在地上:“给我追!就算追到淮西,也要把这些反贼抓回来!”
可少年兵和其他士兵早就跑远了。他们带着抢来的粮,往南走,月光照在他们身上,像给他们镀了层银。少年兵摸了摸怀里的红布,那是赵二狗临死前塞给他的,布上的血已经干了,却像颗跳动的心脏。
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离开的第二天,汝宁卫又有五十个士兵逃走了。有人带着家人,有人带着兵器,都往南走——那里有红巾军,有糙米,有不用啃谷糠、不用被倒卖粮饷的活路。
而李千总的账册,又添了新的一笔:“四月,军粮被劫两千石,叛兵十余人。补征军粮五千石,向流民摊派,逾期不交者,以子女抵账。”
账册的墨迹未干,就被风吹得微微发卷,像在嘲笑这纸上的数字——数字记着粮,记着银,却记不住那些被谷糠噎死的兵,记不住那些被倒卖的粮饷背后,一个个想活下去的人。
黑市的商人还在收军粮,李千总的小舅子还在押送掺沙的粮饷车,可营里的士兵越来越少,空营房越来越多。有老兵在空营房的墙上刻了首诗:“军粮入私仓,士兵啃谷糠。红巾向南去,留此空营房。”
诗刻得歪歪扭扭,却被路过的士兵一遍遍描摹,直到刻痕里积满了尘土,像给那些逃走的、死去的兵,立了块看不见的碑。碑上没写名字,只写着他们共同的渴望——一碗干净的糙米,一身能御寒的甲胄,一个不用把命卖给贪官的世道。
而往南的路上,少年兵和其他士兵终于遇见了戴红巾的人。红巾军的首领看着他们带的粮,又看了看他们身上的伤,说:“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红巾军的兵了。管饭,发粮,战死了,我们给你们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