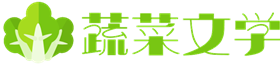简介
喜欢男频衍生小说的你,有没有读过这本《穿越之大唐县令之子逆袭成王》?作者“兽医也疯狂”以独特的文笔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沈澜形象。本书情节紧凑、人物形象鲜明,深受读者们的喜爱。目前这本小说已经连载,赶快开始你的阅读之旅吧!
穿越之大唐县令之子逆袭成王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曲辕犁的成功,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在云阳县乃至周边区域激起了层层波澜。
那日田间试验后,两名老农将所见所闻添油加醋地一番宣扬,“沈小郎君造出神犁,省力又深耕”的消息便不胫而走。起初,大多农户还持怀疑态度,毕竟千百年来犁具皆是那般模样,怎可能说改就改?还变得那般轻巧好用?
沈澜深知空口无凭。他并未急于推广,而是让刘记铁匠铺又加紧打造了五架改进后的曲辕犁,然后做了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他通过县衙发出告示,言明沈家纸坊愿将此五架新式犁具,无偿借予县内最为贫瘠、劳力短缺的五户人家试用一季,只需用时爱惜,秋后归还即可,若试用期间有所损坏,亦无需赔偿。
此告示一出,全县哗然。
无偿借用?损坏勿赔?天下竟有这等好事?那五户被选中的贫苦人家,更是将信将疑,又怀着一丝微弱的希望,领走了那闪着寒光的“神犁”。
在事实面前很快消散。
当那五户人家驾着轻便的曲辕犁,以更少的畜力、更短的时间,将自家以往难以深耕的贫地犁得又深又透时,羡慕和惊叹如同野火般在乡间蔓延开来。尤其是看到其中一户只有老弱妇孺、往年只能粗粗刨开地皮的人家,今年竟也犁出了像模像样的土地时,所有的怀疑都化为了迫切的需求。
“沈小郎君仁义啊!” “这曲辕犁真是宝贝!俺家那犟牛拉旧犁死活不肯走,换这新犁,竟乖乖听话了!” “省下的力气,俺都能多垦半亩荒地了!”
誉之声如潮水般涌向沈家纸坊和县衙。每日都有农户围在纸坊外,或是打听何时能买到新犁,或是向沈澜请教使用技巧。沈澜来者不拒,耐心解答,甚至亲自下示范,将自己琢磨出的技巧倾囊相授。
沈明章借此东风,以县衙名义发布文书,充分肯定曲辕犁之效,并牵线搭桥,协调刘记铁匠铺扩大生产,同时由县衙作保,允许农户以粮食或分期付款的方式购置新犁,极大缓解了贫苦农户的燃眉之急。
一时间,云阳县掀起了一股“换犁”热潮。刘记铁匠铺日夜赶工,依然供不应求。沈澜又毫不藏私地将图纸和改进建议公开给县内其他几家信誉良好的铁匠铺和木工作坊,共同生产,只要求保证质量。此举更是赢得了匠人们由衷的敬佩和拥护。
财富,如同涓涓细流,通过纸坊和曲辕犁的专利分成(虽沈澜坚持低价,但架不住需求巨大),源源不断地汇入沈家。但沈澜的目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敛财。
这一日,他请来了县衙的孙师爷、几位乡老以及李芷云,于纸坊内议事。
“如今纸坊略有盈余,曲辕犁亦初见其利。”沈澜开门见山,“然澜窃以为,独富不如众富。云阳县乃我等桑梓之地,乡梓贫瘠,多有孩童失学,道路泥泞,乡民生病亦难求医问药。澜愿捐出部分收益,于县城设立蒙学堂一所,聘请教书先生,免费招收贫家子弟入学识字;再设一善堂,聘请坐堂郎中,平价甚至免费为穷苦乡民诊病施药;此外,城西通往码头的那段路年年破损,亦可出资修缮,铺以青石,方便行商与百姓。”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
孙师爷和乡老们面面相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设学堂?开善堂?修路?这每一项都是耗资巨大、见效缓慢的善举,寻常富户偶一为之已是难得,沈澜竟要同时进行,而且是长期坚持?
一位乡老颤巍巍起身,激动道:“小郎君……此乃天大善举!功德无量啊!只是……所费甚巨,纸坊初兴,恐难以为继啊……”
沈澜微微一笑,目光沉静而坚定:“老人家放心。纸坊与犁具之利,可持续不断。且此举并非纯然消耗。乡民识字明理,工匠技艺提升,道路畅通,百业方能兴旺。此乃良性循环,利在长远。至于具体章程与管理,还需诸位乡老鼎力相助,共同商议。”
他的目光转向李芷云。李芷云眼中异彩连连,她深深地看着沈澜,轻声道:“小郎君心怀桑梓,目光长远,芷云佩服。墨韵斋愿捐资一半,共襄盛举,并可代为聘请教授蒙学的先生和坐堂的名医。”
有了李芷云的支持,事情立刻变得顺畅起来。乡老们再无疑虑,个个激动不已,纷纷表示必定全力协助,管好用好每一文善款。
消息传出,云阳县彻底沸腾了!
如果说曲辕犁让农户得到了实惠,那么设学堂、开善堂、修路这三项举措,则是惠及全县男女老少的仁政善行!
“沈小郎君真是活菩萨啊!” “沈家积了大德了!” “以后娃儿也能上学堂了!” “再也不用小病拖成大病了!”
赞誉之声如潮水般将沈家淹没。沈明章走在街上,感受到的不再是之前的同情或疏离,而是发自内心的尊崇和感激,腰杆挺得从未有过的笔直,心中对儿子的骄傲无以复加。
在孙师爷、乡老和墨韵斋的共同操持下,事情进展神速。蒙学堂选在了城东一处清净院落,很快传来了孩童朗朗的读书声;善堂请来了两位医术仁心俱佳的老郎中,开业当日,前来问诊的乡民排起了长队;修路的工程也热火朝天地开始了,青石一块块铺就,一条平坦坚固的道路日渐延伸。
沈澜并未置身事外。他时常去蒙学堂查看,甚至偶尔会去给孩子们讲讲算术或简单的格物道理;也会去善堂关心病人的情况;修路工地也常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待人谦和,毫无架子,每每与人交谈,总能切中要害,令人如沐春风。
在这个过程中,他体内的《蛰龙凝元功》似乎也受到了某种滋养,运行得越发圆融自如。他隐隐感觉到,这种为乡梓谋福、获得真心感激的过程,似乎暗合某种自然之道,使得他的心神愈发宁静通透,内息增长的速度竟比单纯打坐更快了几分。
云阳县的风气为之一新。以往的死气沉沉被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所取代。百姓对沈家的拥戴达到了顶点,“沈小郎君”的名声甚至传到了邻近州县。
这一日,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来到了云阳县衙。为首的是一位身着青色官袍、气质精干的中年官员,其随从手持的文书表明,他乃是京兆府派下的巡查使,奉命考察关中各州县农桑教化、民情吏治。
这位巡察使刚一进入云阳县境,便察觉到了不同。道路平整,田亩井然,乡民面色红润,言谈间竟少了许多愁苦之色,反而多了几分对生活的盼头。尤其是看到田间那轻便灵巧的新式曲辕犁和农夫脸上轻松的笑容时,他更是大为惊奇。
及至县城,听到满城百姓都在交口称赞“沈小郎君”的仁义之举,看到那书声琅琅的蒙学堂、病人有序的善堂,这位见多识广的巡察使也被深深震撼了。
他立刻召见了权知县令沈明章。
沈明章如今底气十足,不卑不亢地将儿子造新犁、兴纸坊、捐资办学修路设善堂之事,一一道来,当然,略去了其中诸多惊险斗争,只突出其利民惠民之本心。
巡察使听得连连点头,抚掌赞叹:“好!好一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沈县令,你生了个好儿子啊!此子虽无官身,然其行其举,于国于民,功莫大焉!本官定要据实奏报,为你父子请功!”
沈明章激动得热泪盈眶,连连道谢。
巡察使又提出要见一见这位“沈小郎君”。
当沈澜被请到县衙时,巡察使见其年纪虽轻,却举止沉稳,气度从容,言谈间条理清晰,目光清正坦荡,毫无少年得志的轻狂之气,更是暗自称赞。
一番问答,沈澜对农事、匠造、乃至教化民生皆有独到见解,所言皆切实可行,绝非纸上谈兵。巡察使越听越是心惊,越听越是欣喜。
“沈小郎君大才!”巡察使最终由衷赞叹,“屈居一县,实乃埋没。待本官回京,定向朝廷力荐!”
送走巡察使,沈澜站在县衙门口,望着眼前焕然一新的街道和远处忙碌的田畴,心中感慨万千。
他知道,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不再是那个依靠“奇技淫巧”脱困的落魄县令之子。他以实实在在的功绩和仁德,赢得了乡梓的民心,也敲开了通往更高舞台的大门。
蛰龙,已悄然抬头。 而长安的风,终于要吹向这条渐渐腾飞的潜龙了。
京兆府巡察使的赞誉和即将上达天庭的承诺,如同在已沸腾的油锅里又淋入一勺热水,让沈澜之名不仅在云阳县,更在周边州县彻底传扬开来。“匠作奇才”、“仁商义贾”、“少年贤达”种种名号不胫而走。
这一日,云阳县衙门前颇为热闹。修缮一新的青石路已近完工,匠人们正在做最后的平整。蒙学堂散学的孩童嬉笑着跑过,善堂门口依旧有乡民排队等候,一切井然有序,透着勃勃生机。
一名青衫文士,牵着匹瘦驴,风尘仆仆地来到县衙大门外。他约莫三十上下年纪,面容清瘦,目光却湛然有神,颌下三缕微须,虽衣着半旧不新,浆洗得却十分干净,举止间自有一股从容气度。他并未急着递帖求见,而是静静立于一旁,观察着县衙内外的人来人往,听着乡民衙役的闲谈碎语,目光在那“明镜高悬”的匾额和修缮一新的门墙上停留许久,微微颔首。
守门的衙役见此人气度不凡,不似寻常百姓,便上前客气询问:“这位先生,不知来县衙有何贵干?”
青衫文士拱手还礼,声音温润平和:“在下苏振明,陇西人士,游学至此。久闻云阳沈小郎君贤名,心生仰慕,特来拜会,欲谋一席之地,以供驱策。烦请差大哥通传一声。”说罢,从袖中取出一份名帖,递了过去。
衙役听得是来投奔沈澜的,不敢怠慢。近来因沈澜名声大噪,前来投效的工匠、学徒乃至识几个字的书生也有几个,但如眼前这位气度俨然、直言“供驱策”的文人,还是头一个。他连忙接过名帖:“先生请稍候,我这就去通禀沈小郎君。”
此刻,沈澜正在二堂偏厅与孙师爷核算近日善堂及修路的支出账目。听闻又有贤士来投,他并未意外,但接过那名帖一看,只见其上字迹瘦硬通神,风骨嶙峋,绝非寻常读书人所书,内容亦简洁非常,只写了“陇西苏振明顿首”数字,却自有一股不凡气度透纸而出。
“快请。”沈澜放下账目,整了整衣冠。孙师爷亦是精明之人,见状知来者可能非同一般,也肃容以待。
苏振明缓步而入,目光在沈澜面上一扫,见其虽年轻,却神华内蕴,气度沉凝,毫无少年得志的轻浮之气,眼中不由闪过一丝赞赏。他躬身长揖:“山野散人苏振明,见过沈小郎君。”
“苏先生不必多礼,请坐。”沈澜起身虚扶,请其入座,孙师爷亲自奉上茶水。
“在下贸然来访,唐突之处,还望小郎君海涵。”苏振明从容落座,开门见山,“振明游学四方,途经宝地,见闻小郎君改良农具,活人无数;兴办实业,惠及乡梓;更设学堂、开善堂、修道路,仁心义举,泽被一方。心下感佩,故不揣冒昧,毛遂自荐,愿附骥尾,略尽绵薄之力。”
沈澜微微一笑:“先生过誉了。沈某年少识浅,所为不过份内之事,岂敢当先生如此谬赞。不知先生有何以教我?”
苏振明并未立刻回答,而是反问道:“振明观小郎君之所为,造纸以兴利,改犁以厚生,行善以聚望,步步为营,章法井然,绝非寻常少年所能及。然,小郎君可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沈澜神色不变:“略有耳闻,亦曾经历。”
“哦?”苏振明目光微凝,“小郎君可知,如今之风,来自何方?非止于云阳一隅矣。”
他端起茶杯,轻呷一口,继续道:“小郎君之纸,物美价廉,行销渐广,然关中乃至天下,造纸之业盘根错节,多少豪族大家倚之为利薮?小郎君之犁,省力增效,万民称颂,然朝廷工部、将作监,乃至地方官府,于此等新器推行,自有其章程惯例,岂容一白身少年轻易撼动?小郎君善名远播,民心所向,然上官闻之,其心若何?是喜治下有贤,还是忧权柄旁落?”
一连数问,直指核心,句句切中沈澜内心深处隐约的担忧。
沈澜沉默片刻,坦然道:“先生所言,俱是沈某心病。然,总不能因噎废食。利国利民之事,终须有人去做。”
“善!”苏振明抚掌轻赞,“小郎君有此胸襟魄力,振明没有看错人。然则,既要为之,便需谋万全之策,行稳妥之法,方可既成其事,又保其身。”
他放下茶杯,目光变得锐利起来:“小郎君如今所缺,非小利,非微名,乃‘大势’与‘大义’耳。”
“请先生明示。”
“所谓大势,乃朝廷认可,律法保障。小郎君之新犁、之纸术,虽利民生,然无朝廷明旨褒奖推广,无专利之法予以保护,终是小道,易被仿冒攫取,甚至为人作嫁。譬如这曲辕犁,如今云阳皆知出自小郎君之手,他日若有权贵仿造而献于朝堂,贪天之功,小郎君又将如何?”
沈澜眉头微蹙,这一点他确实思虑未深。
“所谓大义,乃名正言顺,立足之地。小郎君虽行善举,然终是一介白身,商贾之流(虽唐代商人地位不像后世那般低,但士农工商的观念依然存在)。长久居于云阳,虽得民心,然于法理体制之外,终是无根浮萍。一旦有强权压境,或朝中风向有变,顷刻间便有倾覆之危。沈县令(权知)官身未复,亦是隐患。”
“先生之意是……”
“当务之急,其一,须借此次京兆巡查使之口,将小郎君之功绩,尤其是曲辕犁之利,上达天听。不求即刻封赏,但求在陛下心中留下一‘巧思利国’之印象。其二,小郎君当谋求一身‘功名’,非为虚荣,实为护身之符。或由沈县令举荐,或以献犁、献纸术为由,求得一‘散官’虚衔,乃至进入国子监、弘文馆等清贵之地镀金,皆可。一旦有了官身功名,便是体制之内,行事便利,宵小亦难轻易动你。”
苏振明语速平缓,却条理清晰,直指要害:“其三,纸坊、犁具之利,可分润地方豪强乃至朝中贵人,结成利益同盟,而非独享其利,如此可减许多阻力。其四,行善之举,可适度借助官府名义,将功德分于上官,使其与有荣焉,而非独揽其身,招致忌惮。”
这一番鞭辟入里的分析,如同拨云见日,顿时让沈澜心中许多模糊的担忧和未来的规划变得清晰明朗起来!眼前这位苏振明,绝非寻常夸夸其谈的腐儒,而是真正精通世情、深谙权谋、能辅佐主公成就事业的实干型谋士!
沈澜深吸一口气,离席起身,对着苏振明郑重一揖:“先生一席话,令沈某茅塞顿开,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沈澜不才,愿虚左以待,恳请先生留下,助我一臂之力!”
苏振明见沈澜如此果决谦逊,眼中赞赏之色更浓,亦起身还礼:“振明才疏学浅,蒙小郎君不弃,敢不竭尽驽钝,以供驱策!”
孙师爷在一旁早已听得心潮澎湃,见状连忙道喜:“恭喜小郎君喜得贤才!此乃天助我也!”
当下,沈澜便为苏振明安排住处,奉为上宾。苏振明也不客气,安顿下来后,立刻便投入工作。他仔细查阅了纸坊、农具、慈善等各项账目文书,又通过与孙师爷、吴伯乃至李芷云的交谈,迅速掌握了沈澜麾下所有产业的详细情况和面临的潜在问题。
不过数日,他便拿出一份详尽的《近期策要》,从如何回复京兆巡察使、如何运作功名、如何调整产业利益分配、如何与州县各级官员打交道,乃至如何规范内部管理、预防弊端,都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建议。
沈澜依策而行,效果立竿见影。与官府打交道变得顺畅了许多,一些潜在的麻烦被消弭于无形。李芷云看过那份《策要》后,亦对苏振明之才表示了高度认可,墨韵斋与沈家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
有了苏振明这位贤才的加入,沈澜如虎添翼,终于可以从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技术改进和长远战略思考上。
他隐隐感觉到,一条更加广阔的道路,正在这位新晋谋士的辅佐下,于眼前徐徐展开。而他的脚步,必将迈出云阳,走向更远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