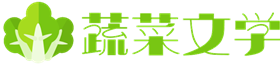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沈慕禾坐在床头,手里捧着那本《道德经》残卷,脑中轻轻拂过“见素抱朴”四个字。这是竹林老者留下的话,几日来,他翻来覆去地揣摩,却总觉得隔着一层薄雾,看不真切。
“素”是本真,“朴”是未雕饰的原木。老者是说,要让心像未经打磨的木头那样,褪去浮华,回归本初吗?
正思忖着,院门外传来一阵喧闹。沈慕禾放下书,走到门口一看,只见张屠户带着两个后生,正堵在苏绣坊门口嚷嚷。
“苏老头,你倒是给句准话!我家阿虎哪点配不上你家晚晴?不就是个穷书生吗,能给她什么好日子过?”张屠户唾沫横飞,手里的杀猪刀往门框上一拍,“哐当”一声,惊得街坊都探出头来看热闹。
苏绣坊的门紧闭着,里面传来苏掌柜压抑的咳嗽声:“张屠户,婚姻大事已定,还请你莫要再来骚扰!”
“已定?我没点头,这事就不算定!”张屠户说着,抬脚就要踹门。
沈慕禾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指节泛白。换作往日,他此刻早已冲上去理论,可想起“不争”二字,想起苏晚晴那句“我觉得害怕”,脚步竟迟迟没有挪动。
他看着张屠户蛮横的样子,心里那股熟悉的火气又在往上冒,像烧得半旺的炭火,灼得他心口发紧。但同时,另一个声音在提醒他:冲动能解决什么?只会让事情更糟。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在心里默念着,目光落在街角那棵老槐树上。树底下有块半露的石头,常年被雨水冲刷,棱角早已磨得光滑,却稳稳地托着树根。
就在这时,张屠户一脚踹开了绣坊的门,拽着苏掌柜的衣领就往外拖。苏晚晴尖叫着扑上去,却被那两个后生拦住。
“住手!”
沈慕禾终究还是动了,但他没有冲上去打架,而是快步走到张屠户面前,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有些意外:“张大叔,强扭的瓜不甜。晚晴姑娘已有婚约,您这样闹,传出去也损您的名声。”
张屠户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沈慕禾会是这个反应。他上下打量着沈慕禾,嗤笑道:“哟,这不是沈家那小子吗?上次没打够,还想替别人出头?”
“我不是替谁出头,只是说句公道话。”沈慕禾迎着他的目光,没有退缩,“您是镇上的体面人,何必跟一个姑娘家计较?若是传出去,说张屠户仗势抢亲,以后谁还敢买您的肉?”
这话戳中了张屠户的痛处。他虽是恶霸,却也在乎街坊生意。他脸上的横肉抖了抖,拽着苏掌柜的手松了些。
沈慕禾又道:“邻村的周书生虽家境普通,却是个秀才,前途不可限量。您家阿虎若是真喜欢晚晴姑娘,不如堂堂正正地比一比,看谁能让她过得好,这才是男子汉的本事,您说呢?”
这番话不软不硬,既给了张屠户台阶,又暗指了他的蛮横。围观的街坊里有人低声附和:“慕禾说得对,强抢可不行。”
张屠户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狠狠瞪了沈慕禾一眼,又看了看周围的目光,悻悻地松开手:“哼,算你小子会说话!这事没完!”说完,带着两个后生骂骂咧咧地走了。
一场风波消弭于无形。苏掌柜捂着胸口连连道谢,苏晚晴站在一旁,看着沈慕禾的眼神有些复杂,有感激,也有惊讶,却没有了往日的害怕。
“多谢你,慕禾。”苏晚晴的声音很轻。
沈慕禾摇摇头:“举手之劳。”他没有多说什么,转身回了家。
走到院门口,他忽然觉得心里那股火气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平静。原来,不打架,也能解决问题。这种平静,比打赢一场架更让他踏实。
“娘,我刚才……”他想把刚才的事告诉母亲,却见沈母正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他那件破了袖口的衣服,一针一线地缝补着。阳光落在她苍白的脸上,竟有种说不出的安宁。
“娘都看见了。”沈母抬起头,笑了笑,“你刚才说话的样子,像极了你爹。”
沈慕禾的心猛地一暖。他走到母亲身边,看着她手里的针线,忽然明白了“见素抱朴”的意思。母亲一生清贫,却从未抱怨过,只是守着这个家,守着他,像一棵朴素的树,默默扎根,不求华饰,却自有力量。这或许就是老者说的“素”与“朴”——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地守住本心。
从那天起,沈慕禾像变了个人。他依旧每天挑水、砍柴、照顾母亲,却多了一份从容。遇到街坊口角,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要么暴躁要么逃避,而是学着用温和的言语劝解,像水一样,慢慢抚平矛盾的棱角。
有一次,药铺的刘掌柜算错了药钱,多收了他两个铜板。换作往日,他定会争执不休,可那天,他只是笑着说:“刘掌柜,许是您忙忘了,这钱您点点。”刘掌柜愣了愣,核对后连连道歉,后来每次给沈母抓药,都特意多放些好药材。
他每日读《道德经》的时间也长了。读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时,他想起自己以前总羡慕镇上富户的绸缎衣裳,羡慕别人有爹撑腰,那些欲望像杂草一样,让心不得安宁。如今想来,粗布衣衫也能蔽体,母亲的陪伴已是最大的福气,何必强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他开始学着简化生活。把院子里的杂草除了,种上母亲爱吃的青菜;把父亲留下的旧木箱擦拭干净,用来存放杂物;连说话也渐渐少了,却更沉稳了。
这日傍晚,他砍柴归来,路过河边,看到几个孩童在水里摸鱼,其中一个不慎滑入深水区,吓得尖叫。岸边的孩子慌作一团,竟没人敢下水。
沈慕禾心头一紧,想也没想就冲了过去。他水性不算顶尖,却也熟悉这条河。他纵身跃入水中,游到那孩子身边,一把将他托起来,奋力往岸边游。
孩子吓得死死抱住他的脖子,好几次差点把他拖下水。沈慕禾憋住气,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把孩子带回去。他想起《道德经》里“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此刻心里没有丝毫慌乱,只有一种冷静的坚定。
终于,他将孩子推上岸。自己却因为力竭,被水流带着往下游漂了一段,才挣扎着爬上岸。
“多谢大哥!”孩子们围着他,又惊又喜。
沈慕禾摆了摆手,刚想说“没事”,却忽然看到岸边站着一个人——正是那日竹林里的老者。
老者依旧穿着粗布麻衣,手里拿着那个破旧的葫芦,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沈慕禾心里一动,连忙走过去,拱手行礼:“前辈。”
“你这小子,倒是把‘慈’字记下了。”老者捋着胡须,“见素抱朴,不光是守己,更是在该出手时,能忘了自己。”
沈慕禾恍然大悟。他刚才救人时,没想过自己会不会有危险,没想过会不会被感谢,只是本能地去做,这不就是“褪去私欲,回归本真”吗?
“晚辈愚钝,今日才略有所悟。”
老者笑了笑,忽然话锋一转:“你母亲的病,是不是总不见好?”
沈慕禾一愣,点头道:“是,寻了许多大夫,都只说要静养,却总不见起色。”
“后山深处有种‘还魂草’,能治百病,只是长在悬崖峭壁上,寻常人难以采到。”老者指了指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峰,“你若有胆量,三日后卯时,到山顶的望仙台来,我或许能指给你看。”
沈慕禾心里掀起惊涛骇浪。母亲的病是他最大的牵挂,老者竟连这个都知道!他看着老者深邃的眼睛,忽然明白,这位老者绝非普通的山野老人。
“晚辈多谢前辈指点!”他深深一揖,“纵使刀山火海,晚辈也定去采来!”
老者却摇了摇头:“采不采得到,看的不是胆量,是心。记住,‘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到了望仙台,莫要忘了这句话。”说完,他转身走向暮色中的山林,身影很快融入光影里,只留下一句缥缈的话:“望仙台,望的不是仙,是己。”
沈慕禾站在河边,望着老者离去的方向,心里既有对母亲病情的希望,也有对未知的忐忑。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被水泡得发白的手,又摸了摸怀里的《道德经》残卷,眼神渐渐坚定。
无论前路如何,为了母亲,他都要去闯一闯。
而且他隐隐觉得,这望仙台之行,或许不只是为了还魂草,更是他求道路上的一道关卡。
三日后卯时。
沈慕禾揣着干粮和绳索,踏着晨露往山顶爬。山路崎岖,怪石嶙峋,好几次他都差点滑倒,却总能在稳住身形的瞬间,想起“轻则失根”四个字,脚步便愈发沉稳。
爬到半山腰时,忽然刮起一阵狂风,吹得他睁不开眼。风中夹杂着碎石,打在身上生疼。他下意识地想退缩,却想起母亲咳嗽的模样,想起老者的话,便俯下身子,像山岩上的青松一样,牢牢扎根在地上,任凭狂风呼啸,自岿然不动。
风停时,天边已泛起鱼肚白。他抬头望去,望仙台就在不远处的悬崖边,云雾在脚下翻滚,仿佛真能通往仙境。
他定了定神,一步步走上望仙台。
台上果然站着那位老者,正背对着他,望着远处的云海。
“你来了。”老者转过身,眼神里带着一丝赞许。
“晚辈如约而至。”
老者指了指悬崖对面的峭壁:“看到那丛紫色的草了吗?那就是还魂草。”
沈慕禾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百丈开外的悬崖上,果然有一抹紫色,在云雾中若隐若现。那地方三面凌空,只有几根枯藤垂下来,看着就让人头晕目眩。
“怎么过去?”他问道。
老者却没有回答,反而从怀里掏出一本线装书,递给沈慕禾:“这是《道德经》全本,比你那残卷更全。你若能在日落前采回还魂草,这本书便送你,也算你我师徒一场。”
“师徒?”沈慕禾震惊地看着他。
老者微微一笑:“你既已悟‘不争’,守‘素朴’,存‘慈心’,便有了入道的根基。只是这求道之路,远比爬这座山更难,你怕吗?”
沈慕禾握紧了手里的绳索,看向悬崖对面的还魂草,又想起母亲的笑容,朗声道:“不怕!”
老者点点头:“好。记住,心不躁,手不抖,脚不浮,方能成事儿。”
沈慕禾深吸一口气,将《道德经》全本小心地揣进怀里,然后将绳索一端牢牢系在望仙台的老松树上,另一端系在自己腰间,深吸一口气,朝着悬崖对面攀去。
云雾在他身边流动,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深渊。他每移动一步,都全神贯注,摒弃所有杂念,眼里只有那丛紫色的还魂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稳住,再稳住。
这或许就是老者说的“躁则失君”——心若浮躁,便会失去主宰,坠入深渊。
当他终于抓住那丛还魂草,将其连根拔起时,朝阳恰好冲破云层,金色的光芒洒满悬崖。他看着手里的还魂草,又看了看远处的云海,忽然觉得,这一路的艰险,早已比草药本身更有意义。
他安全返回望仙台时,老者正坐在石头上,悠闲地喝着酒。
“看来,你不仅采到了草,更守住了心。”老者接过还魂草,又将一个小玉瓶递给沈慕禾,“把草捣碎了,用这玉瓶里的泉水冲服,你母亲的病,不出三日便能好转。”
沈慕禾接过玉瓶,只觉得入手温润,里面的泉水隐隐散发着清香,绝非寻常之物。他对着老者深深一拜:“多谢师父!”
老者哈哈大笑:“我道号玄谷子,你既入我门下,便需记住,修道先修心,心正则道成。他日若有所成,莫忘今日之‘素’,莫失今日之‘慈’。”
沈慕禾郑重地点头:“弟子谨记师父教诲。”
朝阳升起,照亮了望仙台,也照亮了沈慕禾脚下的路。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人生不再只是柴米油盐,更有了一份沉甸甸的道心。而那本《道德经》全本,就像一把钥匙,即将为他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