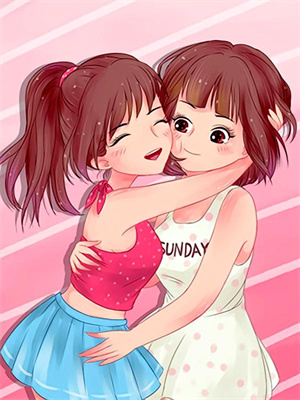简介
《刀光起边尘》由看小说的朕所撰写,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也是一部良心小说推荐著作,内容不拖泥带水,全篇都是看点,很多人被里面的主角沈砚之所吸引,目前刀光起边尘这本书写了102849字,连载。
刀光起边尘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朔风卷着雪沫子,打在“迎客来”酒肆的幌子上噼啪作响。沈砚之将最后一块炭添进火盆,通红的火光映着他左脸那道从眉骨延伸至下颌的疤,像极了半截生锈的铁剑。
“客官,再来碗烧刀子?”店小二搓着手凑过来,眼瞟着沈砚之腰间那柄用旧布裹着的长条物事。江湖人都知道,那布下裹着的定是剑,而且是柄见了血的好剑。
沈砚之没抬头,只从怀里摸出枚铜板拍在桌上。三年前他退出江湖时,剑匣里的“碎影”被仇家熔成了废铁,如今这柄是从旧货摊淘来的残剑,剑脊上有道寸许深的豁口,却比当年那柄名剑更称手。
酒刚斟满,门帘被人撞开,风雪裹着三个黑衣人大步流星闯进来。为首那人面有刀疤,腰间悬着块青铜令牌,上面“影卫”二字在火光下泛着冷光。
“奉镇北王令,缉拿钦犯沈砚之。”刀疤脸的目光扫过酒肆,最后落在沈砚之身上,“阁下左脸有疤,腰间佩剑,该不会就是当年血洗王府的‘断水剑’吧?”
沈砚之端着酒碗的手顿了顿。三年前镇北王勾结外敌,他夜闯王府欲取其首级,却中了埋伏,虽杀了二十三名护卫,终究让那奸贼逃脱。此后江湖便再无“断水剑”,只有在边关小镇混日子的沈砚之。
“认错人了。”他仰头饮尽碗中酒,火炭在盆里爆出火星。
刀疤脸冷笑一声,抽出腰间钢刀:“是不是,拆了你的骨头便知!”
钢刀带着破风之声劈来,沈砚之身形微侧,腰间旧布无风自动。寒光乍现间,残剑已抵在刀疤脸咽喉——那道剑脊上的豁口,正好卡在对方喉结处。
另外两名影卫抽刀欲上,却见沈砚之手腕轻抖,残剑在刀疤脸颈间划出细血线:“镇北王派你们来,是让你们送死的?”
刀疤脸额头冒汗,喉结滚动却不敢动弹。他方才明明看见对方拔剑的动作慢如老妪,偏生自己的刀就是递不出去。
“回去告诉那奸贼,”沈砚之收剑回鞘,旧布重新裹紧剑身,“三日后雪停,我去王府取他项上人头。”
影卫连滚带爬地消失在风雪里。店小二瘫坐在地,看着沈砚之将那枚铜板重新揣回怀里,火盆里的炭渐渐熄灭,只余下几点暗红火星,映着他脸上那道疤,竟有了几分当年“断水剑”的凌厉。
沈砚之推开木门,风雪瞬间灌进领口。他抬头望了眼王府方向,残剑在旧布下轻轻震颤,似在渴望饮血。三年避世,终究还是躲不过。也好,就让这柄残剑,了却当年未竟之事。
雪,似乎更大了。
三日后,雪果然停了。
残阳如血,泼在镇北王府的琉璃瓦上,融雪顺着飞檐滴落,在青石板上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像未干的血迹。
沈砚之站在王府外半里地的老槐树下,旧布裹着的残剑斜挎在腰侧。他看了眼王府朱漆大门前那两尊张牙舞爪的石狮,石狮眼窝积着残雪,在暮色里透着股森然。
三年前他闯王府时,这石狮前还没有那队铁甲卫兵。此刻二十名卫兵手按刀柄,甲胄上的寒霜反射着最后一点天光,连呼吸都带着白气,纹丝不动如泥塑。
“断水剑”的名号,当年在江湖上能止小儿夜啼。可真正让镇北王忌惮的,从来不是他的剑,是他手里那卷账册——记录着镇北王私通北狄、倒卖军粮的铁证。
那年他在王府偏院的密格里摸到账册时,后院突然燃起冲天火光。等他杀开一条血路冲出来,账册已被烧得只剩半卷,怀里揣着的,是镇北王亲印盖过的交割文书,边角还带着焦痕。
“沈爷,里头都探清了。”一个裹着灰袍的瘦高汉子从树后闪出,帽檐压得极低,露出的手背上有块月牙形的疤。是老鬼,当年跟着他混过江湖,如今在王府后厨当杂役。
“西跨院的暗哨撤了,换成了‘铁布衫’马奎的人。”老鬼声音压得像蚊子哼,“王帐设在正厅,听说请了‘鬼手’苏三娘守着,那婆娘的毒针……”
沈砚之点点头。马奎的铁布衫刀枪难入,却怕指关节发力的寸劲;苏三娘的毒针霸道,可她左肩旧伤每逢阴雨天便发,今日雪停转寒,正是她最虚弱的时候。
这些,都是当年在江湖上混熟了的底细。
“账册呢?”沈砚之问。
老鬼喉结滚了滚:“没找到。但王帐里多了个紫檀木匣子,上了三道锁,由镇北王亲自抱着。”
沈砚之扯了扯嘴角,露出点冷意。那半卷账册他当年藏在了城外破庙的佛像肚子里,镇北王找不到,自然以为还在他身上。这紫檀匣子,八成是诱饵。
暮色渐浓,王府亮起灯笼,昏黄的光透过窗纸,映出人影晃动。沈砚之拍了拍老鬼的肩:“你先撤。”
老鬼没动,从怀里摸出个油纸包塞给他:“刚出炉的肉包子,垫垫。”油纸破了个角,露出里面油津津的肉馅,热气混着肉香钻出来,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
沈砚之接过包子时,指尖触到老鬼手背上的月牙疤——那是当年为了护他抢出账册,被北狄人砍的。
他咬了口包子,肉汁烫得舌尖发麻,却暖到了胃里。三年来他啃过冷硬的窝头,喝过掺雪的烈酒,倒忘了热包子是什么滋味。
“走。”他再开口时,声音里那点冷意淡了些。
老鬼最后看了眼王府,转身没入暮色里,灰袍像片枯叶,瞬间消失在巷弄拐角。
沈砚之将剩下的包子塞进怀里,拍了拍腰间的残剑。旧布下的剑身似乎又在轻颤,这次不是渴望饮血,倒像是在催他——别等了。
他矮身,像只蓄势的豹子,贴着墙根滑向王府侧门。那里本该有个狗洞,是当年他为了方便查探,让老鬼偷偷凿的。
果然,侧门墙根处的雪薄了些,隐约能看见块松动的青石板。他刚要伸手去搬,头顶突然传来破风之声。
三枚透骨钉带着寒气射来,钉尖泛着蓝汪汪的光——淬了毒。
沈砚之足尖点地,身形陡然拔高,贴着墙檐翻上屋顶。瓦片上的残雪被他踩得簌簌落下,刚站稳,就见对面屋脊上立着个穿黑衣的女人,手里捏着个铜制针筒,正是“鬼手”苏三娘。
她左肩微微耸着,果然旧伤犯了。
“断水剑,三年不见,你的身法倒没退步。”苏三娘声音尖细,像指甲刮过玻璃,“可惜啊,今晚就是你的死期。”
沈砚之没说话,反手扯掉裹剑的旧布。残剑在月光下露出真容,剑身斑驳,那道寸许深的豁口像道狰狞的伤疤,却比任何利刃都更让苏三娘忌惮。
她当年见过这柄剑的厉害——在江南烟雨楼,这柄剑(那时还是“碎影”)一剑挑飞她十二枚毒针,剑尖贴着她咽喉划过,留下道至今仍在的细痕。
“镇北王许了你什么好处?”沈砚之终于开口,剑尖斜指屋面。
苏三娘冷笑:“取你首级,赏黄金千两,够我换只新的左臂了。”她说着,右肩微动,针筒里又蓄满了毒针。
沈砚之突然笑了。不是冷笑,是真的笑了,左脸那道疤被牵动,竟有了几分当年在江湖上喝酒时的坦荡。
“你可知,你左肩的伤,是谁打的?”
苏三娘脸色骤变:“你什么意思?”
“当年烟雨楼,你毒针伤了无辜,是我留了手。”沈砚之剑尖微抬,“可镇北王给你的伤药里,掺了‘软骨散’,你的旧伤才会年年发作,越来越重。”
苏三娘瞳孔骤缩,左手下意识按住左肩。这些年她总觉得不对劲,每逢阴雨天,左臂便软绵无力,原来……
就在她分神的刹那,沈砚之动了。
残剑带起一道残影,不是攻向苏三娘,而是直刺她身后——那里的瓦片下,藏着个暗哨,正举着弩箭瞄准他后心。
“嗤”的一声,残剑没入瓦片,只听一声闷哼,暗哨连人带弩滚下屋檐,掉进了王府的花园里。
苏三娘这才回过神,毒针猛地射出。可沈砚之已经不在原地,他像片雪花,顺着屋脊滑下,足尖在飞檐上一点,竟直扑正厅的方向。“拦住他!”苏三娘尖声高喊,声音在寂静的王府里炸开,瞬间点燃了所有灯火。
铁甲卫兵的呼喝声、兵刃出鞘的脆响、马蹄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将整个王府织成一张天罗地网。
沈砚之却像游鱼,在网眼里穿梭。他避开迎面砍来的长刀,残剑顺势一撩,挑飞卫兵的头盔,同时借力翻身,从两名卫兵中间穿过,落在正厅门前。
朱漆大门紧闭,门上铜环在灯火下闪着光。他能听见门内传来镇北王慌乱的声音:“拦住他!快拦住他!”
沈砚之深吸一口气,残剑扬起。
这一剑,他等了三年。
不是为了黄金千两,不是为了江湖名声,是为了那些死在北狄铁蹄下的边军,是为了老鬼手背上的疤,是为了自己左脸这道永远消不去的印记。
残剑劈下,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却像一道惊雷,劈开了沉沉夜色。
门,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