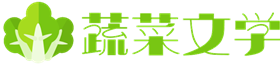第二天清晨,合成闹铃响起时,吴义感受到一种奇异的清醒。昨夜短暂的平静如同假象,褪去后留下的是更深的疲惫,但一种新的、冰冷的决心在其下涌动。他照常起床、洗漱、咀嚼营养膏,动作依旧机械,但内在的某种频率改变了。他不再是那个纯粹麻木的执行单元,也不再是那个被偶然事件击溃的迷茫者。他带上了一层伪装,一层由“观察者”的认知所编织的、更高级别的伪装。
踏入奥米茄公司大楼,恒温的空气再次包裹了他,但这一次,他敏锐地感知到其中蕴含的控制意味。他不再是系统无意识的组成部分,而是一个带着目的潜入的异类。
莱拉依旧热情地打招呼,称赞他“今天气色看起来稳定多了”。吴义回以一个经过计算的、略显疲惫但努力积极的微笑——这符合一个刚刚经历轻微“倦怠”但正在“恢复”的员工形象。他甚至主动提及了埃莉诺推荐的“员工身心优化套餐”,表示“会认真考虑”。莱拉满意地走开了,她的“积极建设性”叙事似乎得到了又一次小小的验证。
坐在纯白的隔间里,吴义启动了系统。客户档案依次展开。今天的第一位客户是一位年轻人, suffering from(受困于)“存在性延迟”,觉得同龄人都在“奔向宏伟目标”,而自己却“找不到起跑线”。
吴义熟练地调出几个叙事模板:“先锋开拓者”、“社群核心缔造者”、“知识边界突破者”。他的手指流畅操作,大脑却像分裂成了两部分:一部分遵循着多年的职业本能,构建逻辑,搭配情感模块;另一部分,则像一个冰冷的旁观者,记录着这一切的荒谬。
他引导着客户,声音平稳,带着恰到好处的共情和鼓励。年轻人最终选择了“知识边界突破者”套餐,眼中重新燃起被赋予的火焰,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站在某个未来领奖台上。
会议结束。客户满意离开。
吴义没有立刻接待下一位。他调出刚才的会议记录和架构方案,目光落在自己设计的那一串串激励性话语和看似自洽的逻辑链上。然后,他做了一件微小而危险的事。
他在方案的终极目标设置一栏,那个通常写着“成就永恒”、“造福世代”、“揭示终极真理”的地方,手动输入了一个极其微小的、几乎不可能被系统自动检测到的概率修正参数:将“目标达成预期满足感持续时间”的模型基准,悄悄下调了0.7%。
这个改动微不足道,甚至可能被归因于模型噪声。它不会影响叙事本身的吸引力,也不会立刻引发客户不适。但它像一颗极细微的沙粒,被投入了完美运行的齿轮中。它基于一个冷酷的观察:所有被赋予的意义,其光芒都会随时间衰减。他只是…更“诚实”地反映了这一过程,哪怕只有一点点。
一整天,他都在进行这种微妙的“校准”。在“家族传承”叙事中, subtly(不易察觉地)增加了一丝对“期望负担”的隐性提示;在“艺术永恒”叙事里,嵌入了一个关于“欣赏者群体必然更迭消亡”的极微弱背景音。这些改动都游走在系统检测规则的边缘,如同在巨大的监视网络下,利用盲点进行的、无声的涂鸦。
他的绩效曲线似乎恢复了“正常”。埃莉诺透过玻璃墙投来的目光,不再那么充满压力。
午休时间,他再次去了那个通风天井。他需要这片相对脱离系统的空间。他拿出终端,再次尝试联系那个匿名者。信息依旧石沉大海。但他不再像之前那样焦虑。他意识到,那种联系本就是偶然,如同夜空中两颗流浪星辰的短暂交汇。真正的“看见者”,或许都像利奥和梅一样,习惯于沉默和隐匿。
下午,一位新的客户被接入。资料显示,这是一位高阶政府官员,购买的是一项高度定制化的“历史使命叙事”,要求能极大激发其责任感和行动力,以推动某个关键的能源分配法案。
吴义照常工作,构建着一个关于“负重前行”、“塑造未来”、“关键抉择”的宏伟故事。但在最后的情感激励模块校准阶段,他鬼使神差地想到了“锈带”那些低矮的建筑、浑浊的空气、以及那个在垃圾回收口寻找食物的麻木身影。
他的手指停顿了。
系统提示他进行最终确认。
就在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决定。他没有像对待其他客户那样进行微小的、消极的“校准”,而是选择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路径。他移除了模块中几处关键的、关于“必然成功”和“广泛拥戴”的强化暗示,取而代之的,是植入了几个极其隐晦的、关于“孤独”、“质疑”和“可能存在牺牲”的意象。这些意象并非负面,反而被包装成“伟大使命的必要代价”、“先知先觉者的宿命感”,使其在叙事逻辑上依然成立,甚至增添了一丝悲壮色彩。
但这细微的改动,彻底改变了这个叙事套餐的情感基调。它不再提供纯粹的、盲目的激励,而是注入了一丝…不确定性和沉重的阴影。这不再是系统标准意义上的“有效解决方案”。
他点击了确认。
几乎在瞬间,系统界面弹出了一个黄色的提示框,并非红色警报,但足够引人注意:
【警告:检测到方案ANM-7747情感激励模块存在非标准参数组合。偏离优化基准12.3%。可能影响预期效能。是否重新校准?】
吴义的心跳漏了一拍。他低估了系统对高阶客户方案的监控灵敏度。
他深吸一口气,手指悬停在“取消”和“重新校准”之上。
就在这时,他的个人终端,那个用于私人通讯的设备,极其轻微地震动了一下。不是工作系统,而是那个加密频段。
只有两个字,来自那个沉寂的匿名者:
“偏差。”
吴义瞳孔微缩。他立刻切断了工作系统的网络连接(利用了一个短暂的、维护造成的延迟窗口),然后迅速点击了“取消”,并手动将方案回滚到了上一个稍早的、未修改的版本。他赶在系统再次扫描前,用标准版本完成了提交。
黄色的警告框消失了。
方案正常归档。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但吴义的背后惊出了一层细汗。那个匿名者不仅还在,而且似乎能近乎实时地感知到他在系统内部制造的…“偏差”。他是在警告?还是在…认可?
下班时分,吴义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疲力尽。这种在刀尖上行走的伪装,比纯粹的麻木要消耗更多能量。
他走出公司大门,融入下班的人流。悬浮车流依旧无声滑行,全息广告牌依旧闪烁。
在街角等交通灯时,他无意中瞥见旁边广告牌上一个宣传最新虚拟旅行的广告。画面美轮美奂,足以让人忘记一切烦恼。
但就在那广告画面切换的瞬间,极其短暂,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秒,甚至更短,在下一帧精美画面覆盖上来之前,他好像看到了一帧闪烁的、扭曲的图像——
像是那张天花板上的水渍,没有五官的脸。
交通灯变绿,人群推动着他向前。
吴义猛地回头,死死盯着那块广告牌。它正正常地播放着碧海蓝天的诱惑。
是错觉吗?是因为过度疲劳而产生的幻视?还是…又一个“信使”般的闪现,一个系统漏洞中溢出的真实?
他站在原地,任由人群从他身边流过。
世界的虚假幕布,似乎因为他持续的“看见”,而开始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不稳定。
他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
但他知道,他制造的“偏差”,或许不仅仅存在于他设计的叙事方案里,也开始出现在他的感知里。
而这,可能是最危险的一种“不规则”。